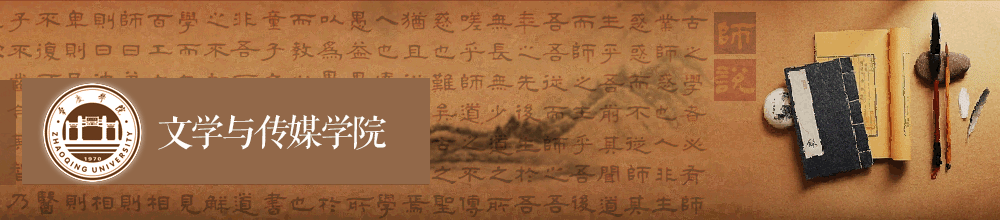【提要】左翼文学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文艺思想,广泛而深刻地表现社会人生的各个方面,积极探讨社会中人性问题和社会伦理的转型,以独特的创作视角构建了左翼文学的革命话语体系和文学意义模式。
【关键词】左翼文学 革命 人生 人性
一、革命:文学意义生成的动力
在30年代的左翼文学话语中,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成为现代作家分析社会的主要知识资源,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支撑着现代作家现实政治行为和叙述重构现实的写作行为。隐藏在左翼文学话语背后的是深刻的现实革命的政治企图,无产阶级革命构成左翼文学创作意义生成的内在动力。三十年代走上文坛的一批青年作家,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指导下,在鲁迅先生的教导与鼓励下,自觉地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以自己曾经经历的惨痛生活为文学叙事的人生经验,关注社会现象,反映社会问题,表现改革社会的强烈愿望,以批判与战斗的精神表达了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面貌和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在左翼作家中,茅盾是主张全景式反映社会人生的主要理论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坚持文学研究会的基本文学主张,始终把文学看成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是反映人生、探讨人生、指导人生的“一种事业”。在他的小说中,全面的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和阶级关系、经济潮流的变化、社会文化道德观念的转型与阵痛这些社会“全息”图像。《蚀》三部曲表现了“现代青年在革命壮潮中所经历的”“幻灭”、“动摇”和“追求”;[1]《虹》要为“中国十年之壮剧,留一印痕”。[2]他的经典作品《子夜》、《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则是“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3]的产品。在茅盾的影响下的这种文学创作模式成为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作家自觉的坚持的文学道路,周文、叶紫、张天翼、柔石等人在鲁迅的关怀和指导下,迅速成为左翼文学的骨干力量,他们以个人的人生经历为创作的题材,广泛反映了当时各个地域的社会状况,以丰富的文学实绩展示了左翼文学的成就,继承和丰富了茅盾所开创的社会剖析类型的创作模式。
30年代左翼文学作家和“五四”时期作家一个最为明显的不同是身份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写作立场的变化。从事左翼文学运动的主要作家大都具有中国共产党员的身份,他们有的是刚刚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从国共两党间惨烈的政治斗争中退下来,转而拿起笔在文化领域继续进行战斗,如茅盾、叶紫等;有的是向往革命的思想急进的青年,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到上海,积极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从事政治斗争之余进行文学创作,如柔石、周文、张天翼等。他们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在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中,从事艰苦而复杂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政治斗争是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这种身份决定了作家观察现实、表现现实、叙述故事时的革命立场以及文学意义生成的方式。他们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并以自己的文学创作来解析、演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30年代左翼文学创作是和政治革命紧密相连的工作,不是纯粹的为文学而文学的活动。茅盾在谈到自己创作《子夜》时说过,当时他从实际工作中退下来,由于眼病和神经衰弱,为了躲避国民党政府的通缉,蛰居在上海的亭子间,闭门不出,从事小说创作,他所关心的仍是现实斗争,他的《子夜》试图思考的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提出的答案是“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4]这种构思
鲍昌宝(1964-),男,安徽庐江人,肇庆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的结果决定了整个小说的故事架构和人物命运,由此也决定了小说的意义功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救不了中国,只有工农革命才是中国救亡运动的主力军。
经典的左翼文学作品普遍关注着各种社会问题,茅盾的《子夜》探讨的是中国社会性质的政治性的命题,交织在《子夜》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是中国工农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他试图用自己的创作证明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之路。他的“农村三部曲”着力反映在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下农村的破产,而农村的土地革命则是农民摆脱穷困命运的唯一道路。吴组缃的小说则是揭示农村家族社会的腐败和破产,封建的礼乐崩坏和家族制度的腐朽注定了封建的农村社会的破产,土匪横行与劣绅的残酷,共同造成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的悲惨命运。叶紫的小说集中在广大的农民在军阀战争中人的基本生命权如何得不到保障,一种草菅人命的社会现象普遍存在。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关注的是经济破产后的农村社会面临的人性的异化和堕落。周文的小说以其独特的川康边地人事书写把旧军阀的腐败与社会的黑暗做了淋漓地揭示。
社会的黑暗、生存的苦难和人民的痛苦成为左翼文学对现实的感知与表达,从这些文学关注的主题和表现出来的倾向来看,左翼作家抱有强烈的社会干预意识,时代的使命感和社会的责任感使他们在建构文学现实的时候,重新界定了生活的本质,他们强调文学的价值是在“表现人生,探讨人生,指导人生”,因为,“如果我们不能明了现代人类的痛苦与需要是什么,则必不能指示人生到正确的将来的路径,而心中所怀的将来的社会理想亦只是一贴不对症的药罢了”,而现代人类的痛苦,“简单地说,就是世界上有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陷于悲惨的境地并且一天一天的往下沉溺。”因此,“文学者的目前使命就是要抓住了被压迫民族与阶级的革命运动精神,用深刻伟大的文学表现出来,使这种精神普遍到民间,深印入被压迫者的脑筋,因此保持他们的自求解放运动的高潮,并且感召起更伟大更热烈的革命运动。”[5]这是左翼作家理解的社会生活本质,他们的创作实际上是期待对这一本质的文学表述能够转化为改造社会振兴民族的精神资源。
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的创作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他们关注社会现实,关注现实中的人生形式,把文学的功能归结为“暴露”和“批判”,从而赋予文学浓厚的政治性价值。隐含在左翼作家所描写的现实生活真实图景背后的是一种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的话语,在他们所表现的社会生活之“是”中潜伏着对未来理想社会“应该是”的形式的呼唤和企盼,并且以“应该是”来同构现实生活之“是”,于是,既存的社会现实便被当成是一种不合理的存在。左翼作家对现实采取基本相似的价值立场:批判和讽刺。由此,一种强烈的变革现实的主题隐逸在文本的深层。正如茅盾所指出的:“一时代的文学是一时代缺陷与腐败的抗议或纠正,我觉得创作者若非是全然和他的社会隔离的,若果也有生活的同情的,他的创作自然而然不能不对于社会的腐败抗议。”[6]
站在暴露和批判社会的写作立场上,选取生活的腐败和阴暗面作为作家重构现实的叙事行为,实际上是为了实现改变现实的政治目的。革命,作为文本的内在逻辑,贯穿左翼作家文学行为的每一个方面。文学,始终是革命者呼唤革命、实行革命的战斗武器。其中,对文学形态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文本中鲜明的敌我对立的阶级分析和阶级仇恨。左翼文学基本采取相同的叙述模式,即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革命者和反革命者之间天然的仇恨和誓不两立。因此,文学中的人物被设计在求取生存的意志与艰难生存的现实之间,生命的悲剧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中反复演绎,从而达到批判社会的政治意识功能。
因此,在左翼文学话语中,现实的政治性功能得到了强化,文学叙述的人生故事和生命形态被有意识地引入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的理论范畴中。“五四”时期文学中所集中关注的“人生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这些形而上的问题被“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农村“丰收成灾”、旧式军队的黑暗腐败等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所取代。随着左翼文学关注的焦点问题走向现实化,“五四”文学中父与子的冲突模式以及所映现的新旧道德观文化观的冲突开始转变为现实社会中的阶级冲突。资本家和工人、地主与农民、军阀与士兵的二元对立和冲突构成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主要的叙述架构。而隐藏在这些“问题意识”和“阶级冲突”的叙事话语背后,是一种深刻的批判社会改造现实的心理焦虑。
二、叙述他者:意识形态化的人生
30年代的左翼文学意义生成的主要动力隐含在革命话语的指向中,他们通过客观冷静的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努力揭示现实社会中隐伏着的革命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从而为中国革命寻找合法化的依据。作家自我消隐在文本之外,仅仅作为叙事者存在,从不越界进入文本层面直接行动。他们试图创造一个和现实世界相对应的文学世界,并且把这个“仿真世界”当作和现实世界完全一致的客观存在,因此,整个文学图像变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他者”。在左翼文学中,作家很少采用第一人称作为叙事的主要行为,而是采用全景式的全知全能式的叙事模式,以一种客观化现实化的方式创造一个仿真型的社会图景,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个社会图景普遍化为整个社会的典型和代表。普通人的生命景观和人生形态由此被成功地结构在文学文本之中。
从揭示革命的必然性和合法性的前提出发,左翼作家对“他者”的叙述构成左翼文学的主要表达策略和政治化的文学价值诉求。他们从各自的个人经验出发,不约而同地以分析的眼光来看待整个社会,把文学世界集中在对社会的黑暗、官僚体制的腐败、下层人民生活的不幸等方面进行表述,所有作家对现实的感觉和价值判断都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此在的现实是不合理的,必须进行革命的清除和荡涤,现存社会经过革命必然走向一个更美好的理想社会形态。
茅盾的《子夜》着意塑造了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英雄”和“王子”形象,呈现的是以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为主体的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全景。在吴荪甫的传奇故事中,展示了一个实业界巨子奋斗、发达、失败的悲剧。吴荪甫的人生悲剧,被嵌定在1930年5月至7月这段真实的历史时间里,当时中国社会和世界上重大的历史事件直接作用于小说文本中的人物命运,贯穿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始终,直接形成吴荪甫悲剧形成的社会原因。茅盾通过对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人生悲剧的叙述,表明了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在中国社会的不可抗拒的命运。他的悲剧是一个阶级的悲剧,他的命运是一个阶级的命运。整个小说便在这个设定好的叙事框架中展开。在这种意识形态化的人生叙事中,《子夜》中的人物形象服从于各自所属的阶级属性,在性格上呈现出相对的单一性、平面化。阶级的符号构成了小说中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及其人物命运。
突出人物性格的某一个方面,把他作为一个阶级的最主要的特征并揭示阶级的命运,成为茅盾及其他左翼作家塑造人物的主要方式。在茅盾优秀的短篇小说《春蚕》中,三十年代中国江浙一带的蚕农的人生图景和性格特征被经典化地结构在“丰收成灾”社会问题框架中,以突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的社会现实给中国农民的沉重打击。老通宝失败的命运显示了自然经济解体时中国农民的悲剧。与此相对照,小说中以多多头为代表的青年农民,他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代表着一种年青农民的生存方式的合理性,即走向革命的人生方式。他的《农村》三部曲中所反映的广阔的农村社会图景和农民的生活方式隐含在强烈的农村革命的叙事话语中。
这种以革命理论为小说创作的思想背景,强调的是对社会进行意识形态的分析,茅盾曾说:“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这转变中的社会,非得认真研究过社会科学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确,而社会对于我们作家的迫切要求,也就是对那社会现象正确而有力的反映。”[7]而对左翼作家来说,这种社会分析的理论资源基本上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为基础的,因此,左翼文学对人生的关注表现为对社会下层人生的普遍同情,对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的生活境遇的集中描绘,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社会性质的揭示。
关注下层社会普通人的不幸遭遇和悲惨命运,对受压迫受凌辱的人生的“实录”,成为左翼作家呼唤革命宣传革命的普遍叙事策略。因此,在左翼文学中,人生的悲剧性得到了广泛的描写和表现。吴组缃便自觉按照茅盾所开辟的描写社会人生的方式进行创作,他说:“中国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小说方面有两位杰出的作家:鲁迅在前,茅盾在后。茅盾之所以被人重视,最大原故是在他能抓住巨大的题目来反映当时的时代与社会;他能懂得我们这个社会。他的最大的特点便是在此。”[8]所谓“懂得这个社会”,就是指用阶级的革命的观念来透视整个社会人生,把人物放在时代的背景中来揭示其性格和命运。他的《一千八百担》就是采取类似《子夜》的社会剖析式的方法进行小说叙事。吴组缃以自己的家乡皖南农村为主要表现对象,深刻揭示了30年代中国农村在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所面临的破产现象,以及在这个破产过程中社会伦理道德剧烈变化。在他的小说中,皖南农村的破败没有令人感伤、忧郁的画面,而是蕴藏着“愤怒”之气,一股挣扎、反抗的烈火正在社会底层蓄积、汹涌。吴组缃的小说最终展示出来的是:中国农村的革命正在不可阻挡地到来。
这种动荡农村中郁结的普遍的愤怒情绪,是30年代左翼作家对中国农村社会的主要关注对象。吴组缃的小说侧重于表现沉滞的农村中人性的乖张和官逼民反的人生道路,叶紫的小说更喜欢把人物放在血与火的社会动荡中展示他们的悲惨命运,揭示他们走向抗争与革命的道路。在《电网外》中,他表现了一个老农民王伯伯安土重迁的心理习惯如何使他遭遇到人生的不幸。《山村一夜》则叙述了一个胆小怕事的父亲在愚昧之中亲自把儿子送给官军希图保全儿子最后儿子却被杀死的悲剧,它以惨痛的教训,启示人民如何抛弃封建的奴性,追求最后的觉醒,并且揭示了官军残酷野蛮的本性以及农民和官军妥协只有死路的结局,从而表达了只有坚持坚定的革命道路,农民才会寻找到自己的真正的出路。
左翼作家都有一种急切的“冲进时代的核心中去”,“在时代的核心中把握一点伟大的题材,来作我们创作的资料”,从而创造出“大众的内容,大众的情绪,一直到大众的技术”[9]的创作冲动,当他们在表现人生时,这种冲动凝聚为对形成革命的社会历史原因的探讨,即他们普遍从社会经济方面来透视农村破产的原因,而且由于他们基本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阐释社会人生的思想资源,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多少都有单一化概念化的倾向,对社会的分析也基本以敌我对立的二元化的思维方式来结构故事的架构。这集中表现为对“丰收成灾”的社会现象的反映。“近来以农村经济破产为题材的创作,自从茅盾先生的《春蚕》发表以来,屡见不鲜,以去年丰收成灾为描写中心的,更特别的多,在许多刊物上常见发表。本刊近来所收到的这方面的稿件,虽未经过精密的统计,但至少也有二三十篇。”[10]其中,在文学史上较为知名的就有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夏征农的《禾场上》、叶紫的《丰收》、蒋牧良的《高定祥》等。如此众多的左翼作家普遍关注这个题材,是因为其中所蕴含的戏剧性使作家能够从容把握时代问题的命脉:导致农村经济破产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而对人祸的探讨就是推动社会革命的重要问题。
以社会分析的眼光来叙述中国农村破产中农民的不幸的人生,并把造成这种悲惨的命运的原因归结为统治阶级的残暴与冷酷,使得左翼作家在表现社会人生形态时建构了独特的叙事空间,他们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立场,把整个叙事话语看成是阐释革命理论的基本策略,因此,在阶级对立中生产了一个个社会下层人生的故事,而这些人生故事隐含着作者对时代精神的理解和概括。
三、人性:左翼文学的道德关怀
左翼文学在广泛地进行社会的阶级分析时,书写了大量的下层人民的不幸和悲惨的遭遇,在关注他们现实命运的同时,左翼文学有着深刻的对社会人生的伦理道德关怀,他们深入到人物的心灵层面和精神层面进行人性的透视,并且对人性的内涵进行重新的阐释和深层的反思。隐含在左翼作家的阶级革命话语里,是一种新的社会伦理价值观的构建。
生存问题,尤其是温饱问题,构成左翼文学对人性理解的最基本的内涵。下层社会中人民生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缺失,使左翼作家忧心如焚。在《春蚕》和《丰收》中,老通宝一家和云普叔一家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使全家能够过上富足的生活,同自然和社会进行了艰难而绝望的奋斗。温饱问题成为老通宝和云普叔为之奋斗的最高人生目标,当人生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在顷刻间崩毁,也就表明人性的最后的底线被彻底毁灭。多多头和立秋之走向革命便是人生唯一的选择。在这个基点上,革命是恢复人性的必然之路,是寻求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生存权的合法途径。左翼作家在表现人民的不幸遭遇和悲惨生活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生存权的失去,并把这个问题作为人性的基本内涵来表达。叶紫在《电网外》中通过王老伯伯的人生遭遇,试图证明:只有起来革命,才是真正符合人性捍卫人性的选择。吴组缃的小说以凄婉的笔调写出了残酷的生存境遇中人性如何被扭曲。当人民在无路可走时,左翼作家不得不拿出人性中最神圣的一张牌,让蛰伏在幽暗角落里几千年的兽性跳出来,进行最后的抗争,革命就成为最富有人性的行为。
在关注下层人民为了物质上生存基本权利缺失进行殊死的搏斗的同时,左翼作家对下层人民精神上的磨难以及被传统文化奴役的精神上的创伤进行了有力的揭示,从而深入到精神层面表达对人性问题的充分关注。在吴组缃小说中,下层妇女的不幸在淡淡的悲哀中被缕缕讲述出来:《卐字金银花》中描写了一个年轻守寡、偷情怀孕的女性,为讲究名教的家族所不容,最后凄惨而死。在《菉竹山房》中,礼教的压抑与心灵深处的欲望如何折磨着年轻的生命,小说在充满“鬼气”的描绘中显现了浓郁的人性残缺的悲凉。叶紫的小说更注重揭示残酷的现实中人性的坚持所带来的生命悲剧,在《丰收》中,云普叔安分守己、勤劳朴实,恪守天性中的善良,最后只能任人宰割,辛苦劳动所得被人白白抢走,普通的人性坚持变成了剥削阶级对下层人民进行肆意掠夺的同谋。《电网外》中的王老伯伯为了守住家园中的小小产业经历了家破人亡惨祸。对他来说,家园便是生命安身立命之所,是幸福平安的象征,然而,这微末的愿望却成了生命的累赘。在叶紫的小说中,人性中善良和纯朴往往都是生命悲剧的直接原因,传统人性的内涵被看成是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的最便利的工具,因此,在阶级社会中,如何建立新的社会伦理价值体系和新的人性关怀便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命题。
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也许是左翼文学对伦理关怀最为深刻的作品之一,它以男女之间“性”关系的不平等造成中国女性的悲惨命运为切入点,探讨了中国社会在政治革命的同时,进行伦理革命的迫切性。小说以浙东民间普遍存在的“典妻”为基本叙事框架,反映了经济破产的农村下层人民为了生存出卖尊严的非人生活,细致表现了贫困的生活与“典妻”习俗如何损害了女性的神圣的感情。在《为奴隶的母亲》中,下层社会的人民,在贫困的物质生活中,为了获得简单的生存条件,精神上受到的极度凌辱和折磨:贞操可以典当,人格可以典当,神圣的母爱也随之撕裂。
从阶级斗争的立场出发,反思整个社会的不合理的存在,关注人性的内涵,是左翼文学对人性抒写的独特之处。周文的“川康边地系列小说”,全面揭示人的生存状况的艰难和人性的恶浊,进而探讨国民的劣根性,构成左翼文学改造社会改造人性的另一极。在周文的小说中,恶劣的生存环境和污浊的社会现实中,生活着一群卑鄙龌龊、凶残险恶的人们,他们为着个人的私利,愚昧、残忍、缺乏同情心,在川康边地特定的地域中演绎着人生的悲喜剧。在长篇小说《烟苗季》中,周文叙述了一群毫无人性的人物的鬼魅化生活,他们人与人之间没有诚信,没有同情,没有仁慈,有的是凶残和险恶,结党营私,尔虞我诈,从而表达对军阀统治的混乱与黑暗的愤恨与诅咒。在这个“丑恶”“开垦”的无人性世界里,卑鄙与无耻、荒诞与无聊肆意横行。
与军阀的无人性的世界相比,下层民众的内心世界中却时刻闪现着人性的光辉,虽历经人生的磨难与生存的艰难,人性的追求永不可泯灭。周文的《山坡上》深刻地发掘了兽性中人性的觉醒,在人类的残酷中发现人类永远的爱心。小说描写军阀战争中两支敌对的军队互相残杀的情景,没有正义与邪恶区分,两边的士兵半是被迫,半是出于职业习惯,彼此攻伐、杀戮。李占魁和王大胜分属于战争的两方,两人为了生存,展开了一场恶战:李占魁被王大胜打得昏死过去,王大胜的肚皮被刺刀捅破,肠子流了出来,也昏死了。当李占魁苏醒过来,第一个念头便是你死我亡的复仇,但当他发现遍地的野狗准备吞食王大胜时,他突然可怜起自己的死敌,并用石块与野狗搏斗,最后终于抓住王大胜的手,喊了一声“弟兄”,王大胜感到李大魁手中的暖流,眼角滚下了热泪。两人由不共戴天的仇敌变成了相濡以沫的朋友。小说以奇特而残酷的场面,暴露了战争的残酷,并在这残酷中揭示潜藏在兽性中的人性的复活。
这种基于同一社会地位而生发出的阶级感情,标明左翼文学正在构建一种以阶级利益为共同体的新的社会伦理道德雏形。在张天翼的《二十一个》中,满腔仇恨的士兵觉醒了,他们不再为混战的双方军阀卖命,而是团结起来,互相扶持,互相救助,心连心,寻找新的人生出路。在《仇恨》中,背井离乡的难民一路在痛苦与咒骂中军阀,他们怀着深仇大恨,怀念被军阀糟蹋的田园,痛悼被军阀拉夫和奸杀的亲人。但他们也有深挚的同情,看到一个被军阀拉夫而累垮又挨刀砍伤奄奄一息的难民,便不顾所带的饮水缺少,为他冲洗伤口,抬着他一起逃亡,表达了穷苦的人“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的阶级感情。他们痛恨给他们苦难的军阀士兵,发现三个溃逃的士兵,便发疯地冲上去围打,愤怒地要吃他们的肉。当明白了这些士兵也是种田人,在旧军队中一样受欺辱,打仗也是为军阀当炮灰,便给予了深深的同情。这一群“都一样是受害者”的人怀着共同的命运感,埋藏了同伴,牢牢地凝聚在一起,在昏黑的天地间寻找着穷苦人的活路。小说中,无论是深切的爱和强烈的恨,都散发着贫苦的受害者的未泯的人性。
张天翼在左翼文学中的独特价值是以喜剧的笔调充分揭示了中国社会中传统伦理道德的崩溃,显示了一种深刻的社会伦理关怀。在《脊背和奶子》、《砥柱》中,他犀利地讽刺了在礼教名义下封建权势者的虚伪与卑下的品性,受侮辱者被戴上淫邪的罪名,男盗女娼者却成为社会道德的化身,从而宣判了旧的社会伦理的死亡。在《包氏父子》中,张天翼以敏锐的目光透视中国社会中的家庭结构中人伦秩序的消解,通过包氏父子之间的乖戾的关系的描写撕破了宗法制社会中“望子成龙”的文化心理,从而深入到传统人性内涵中最基本的环节——父子关系层面暴露传统人性观的虚妄。小说通过父子两代人伦理价值的错位揭示了传统的“望子成龙”、“光宗耀祖”的伦理价值观的腐朽与虚妄,也批判了现代以享乐为中心的伦理价值观的荒诞与庸俗。在《包氏父子》中,隐含着张天翼对现实人生伦理价值缺失的深深的焦虑。
当左翼作家在广泛地批判社会生活中非人性的现实时,支配其话语中心的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性的重建和信仰。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在这方面是一个可贵的探索。在《上海屋檐下》,夏衍全面关注现代社会中的人性问题的各个方面,并且围绕革命者匡复的情感悲剧和人生道路的选择,提供了一种新的人性伦理范型。作品在一种淡淡的忧郁和无奈中,描写了上海一幢弄堂里五户人家在阴郁的黄梅季节里的一天的日常生活和平凡生存的喜怒哀乐,真实地展现了三十年代中国社会中灰色的生活图景。在这里,生活是如此沉重,获取生存的基本需求是如此艰难,而潜隐在下层群众中的人性的光辉却在阴沉的现实黑暗中生发出夺目的异彩。施小宝是一个沦落天涯的弃妇,无依无靠,在生活中倍受流氓无赖的欺辱;李陵碑是一个由于儿子被抓壮丁战死而借酒浇愁的孤苦老人;正在失业的生活无着的黄家楣;被捕入狱而妻离子散的匡复;走投无路为了生存不得不抛弃爱情的坚贞委身再嫁的杨彩玉;和朋友的妻小同居,在工厂受到倾轧,良心受到折磨的林志成,等等,他们都是被生活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平民百姓。然而,在他们身上,却具有人性中最可宝贵的情操。其中,黄家楣一家的故事最为凄惨动人。黄父是个忠厚、善良、富于牺牲精神乡下人,他辛辛苦苦地把儿子拉扯大,供养黄家楣到大学毕业,本以为能在上海有了出息,千里迢迢赶到上海来看儿子,却不料儿子正失业在家,穷困潦倒。儿子、媳妇孝顺、体贴。为了不让父亲知道自己的窘境,强颜欢笑,不断掩饰,当他们典当唯一的一套“出客”的衣服被老父亲看见时,父亲把自己仅有的几个钱留下来,悄然回到乡下。善良的灵魂的悲剧既是对社会黑暗的有力的控诉,又是人性美的无声赞歌。而主人公匡复和杨彩玉的悲剧却是三十年代广泛存在的政治迫害所造成家庭悲剧。主人公匡复和杨彩玉是在现代爱情观念下自由结合的志同道合的夫妻,他们曾有着共同的信念,革命的生涯使他们的生命充满着浪漫的激情,然而,随着匡复被捕,在监狱里呆了八年,杨彩玉为了生活,不得不和匡复的朋友林志成结婚,从此沦落为一个平庸的家庭主妇,而匡复由于长久的牢狱生活,也意气消沉。当匡复从牢狱中出来,发现自己的妻女已经和朋友林志成组成了新的家庭。经过艰难的情感痛苦,他终于重新鼓起革命的热情,主动告别了妻女,继续为改造社会而奋斗。在夏衍的叙事中,革命才是唯一解救平淡庸俗的人生的合理选择,是摆脱生存困境的唯一方式,是重建新的合理的社会的必由之路。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文学不借人,无以表现‘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须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绝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会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11]在左翼文学中,人性的关怀是和对整个社会现实的分析批判紧密相连的过程,它从来也不是抽象的无阶级性的人性。人的自然本性只有在人的社会性中才能得到充分的阐释,无论是爱还是恨,都是在社会的阶级对立之中显示出来的。因此,人的自然属性与人的社会属性是有机地相互渗透、融合、纠结的统一体。左翼文学深刻地表现了人的社会属性如何影响、改变、扭曲了人的自然本性,从而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丰富性和深刻性。左翼文学把人性放在社会历史的宏观背景中考察,使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现代社会中的人生和人性问题的思考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
参考文献:
[1]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A].茅盾研究资料(中)[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4.
[2] 茅盾.《虹》跋[A].茅盾研究资料(中)[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5.
[3] 茅盾.《子夜》跋[A].茅盾研究资料(中)[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9
[4] 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A].茅盾研究资料(中)[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8.
[5]茅盾.文学者的新使命[A].茅盾全集(第18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540-541.
[6]茅盾.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C].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2(45).
[7] 茅盾.我的回顾[A].茅盾研究资料(上)[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77-78。
[8] 吴组缃.评茅盾的《子夜》[C].文艺月刊,1933(1).
[9]叶紫.从这庞杂的文坛说到我们这刊物[C].无名文艺旬刊,1933(1).
[10] 社中日记[C].现代,1932/2(1).
[11]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A].鲁迅全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