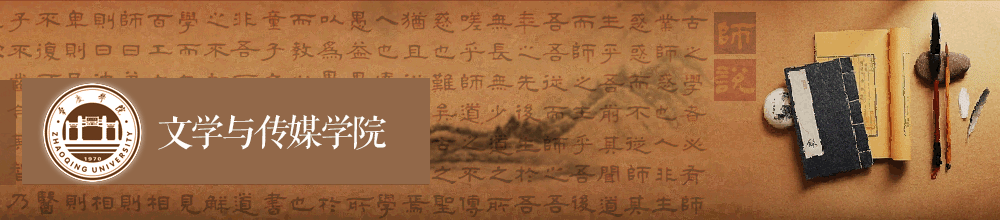市民日常生活诗性的审美发现
――王安忆论
“诗人并不发明诗,/诗在后面某个地方,/它在那里已经很久很久,/诗人们只是将它发现。”[①]理论上讲,日常生活正如诗人詹·斯卡塞尔所揭示的那样,是隐藏着诗性的“在后面某个地方”,作为日常生活主体的普通百姓身上也是深藏着诗意的。然而,日常生活的诗性在很长时间内却没有得到彰显。原因既与日常生活主体大多为老百姓,而百姓日用“道”而不知这一客观事实有关;也与作家的审美情态有关。在以往的宏大叙事或启蒙话语里,日常生活被当作刻板,平庸或工具理性的同义词,毫无审美价值可言,作家对日常生活不是抵抗就是逃避,或者干脆对之加以改造与提纯。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在一些女性小说家的创作中,出现了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新的写作“症候”,她们温情地拥抱日常生活,对日常生活持审美认同的亲和姿态,真诚地探寻日常生活的诗性意义与价值,显示了女性写作新的日常生活叙事伦理。王安忆无疑是市民日常生活审美化写作的代表作家之一,她从1980年的《小院琐记》起,就开始着意铺陈、渲染并诗化市民的日常生活,后经《庸常之辈》、《流逝》、《文革轶事》、《69届初中生》、《流水三十章》以及后期的《长恨歌》、《我爱比尔》、《富萍》、《新加坡人》、《桃之夭夭》等的不倦探索,王安忆建构了一个“有情有信”温馨感人意义丰沛的市民日常生活诗性世界。
一、日常物象世界诗性的发现
“物象”“是一个充分中国化的概念,老子在《道德经》中,赋予了‘物象’亚形而上学的意义,认为它是本体之道在‘恍兮惚兮’之间的直接生成物”。[②]日常物象世界是指人类日常活动所赖以发生的物质对象世界,如弄堂、庭院、家庭、社区、单位、街道工场、商场、影剧院、美食、服饰等。与池莉、方方笔下纷陈扰攘、暗淡喧嚣的日常物象世界,范小青笔下缄默死寂的日常物象世界不同,王安忆所描绘的日常物象世界是一个落花有意,流水含情,充满盎然趣意和生命情调的诗化世界。刘成纪在《物象美学》一书里指出,物象世界诗性化的关键是要建立一种“心物平行、天人凑泊”[③]的新型的审美物象观:一方面需要把实存的物象看作是和人一样的自在生命之物,承认万物都有它的“物意”,即“是本体之道和物的自由本性在对象之物中的充盈”[④];另一方面,也需要审美主体介入物象世界,对物象之“物意”的诗意发现与体认。只有物象的“物意”和审美主体的诗意发现共时存在,本真的物象世界才可能被敞开。海德格尔也曾从人与物的关系维度探讨人的本真存在,他指出人对“物”的征服并不能使人走向诗意居住,人类只有在万物一体的境界里才能获得本真的存在。为此,人要亲近物,了解与尊重物的“物性”。何谓物的“物性”?海德格尔通过对水壶的“物性”分析,指出物的“物性”就是接受、保存和倾出、馈赠的双重聚集,即物的自由本真的存在。[⑤]
王安忆是深谙这种物象诗性的创造规律的。而王安忆的上海经验和女性身份又使她对日常物象的诗性化成为可能。上海,作为一个“华洋错综,新旧掩映”的现代中国摩登都市,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它的花团锦簇、精致时尚、光鲜灿烂的物质世界,这就给王安忆诗化物象提供了可能;而女性细致敏感的天性以及与日常生活的天然联系,又使王安忆能以审美的情怀感受日常物象世界:一方面她积极调动自己发达的审美感觉,发现沉默无声的物象的“物意”或“物性”;另一方面她充分发挥自己把握事物生动具体的细部特征的杰出能力,将自己温婉丰沛的感情投射到物象世界的细枝末梢中,让这些微观的物象随着她的情感诗意地起舞飞扬。
在儿童天真、幻想、灵性、自由的诗性思维看来,沉默无言的里弄,“就像我们的躯壳,收藏着我们的灵魂。”[⑥]巴掌大的庭院“是个美妙的小世界。是我的庇身所。”[⑦]因为弄堂、庭院不仅是她们游戏的乐园,也是她们生命的乐园。她们在弄堂跳绳,踢毽子,造房子、翻筋斗,在庭院种石榴、玉米、向日葵、蓖麻和葱,养育茂盛的车前子等,这些活动使她们获得许多难以忘怀的生活乐趣和生命的快乐体验。即便是后弄以它的阴沉与寂寞给她们造成了压抑与恐怖的生命体验,在王安忆的审美关照下,它也仍然是富有诗意的,“冲突之后达到和解,身心都将焕发和平光辉。这是一种深刻的安宁,经历了残酷的斗争之后,终于获得。”[⑧]在此意义上,沉郁的后弄正是儿童日后走向平和与安宁的生命居所。这就是王安忆在《69届初中生》、《忧伤的年代》、《流水三十章》、《桃之夭夭》等多个文本里,借助儿童视角对弄堂以及庭院所做的审美判断。换句话说,在儿童的审美畅想里,弄堂、庭院的物性就不仅仅是实用的物质建筑,而是能娱悦儿童的目光,抚慰儿童孤独忧伤的心灵,护卫儿童生命成长的审美化的生存场所,与“文革”时期混乱无序的街道形成了鲜明对比。
除了用天真幻想的儿童诗性思维使沉默的日常物象携带上审美光辉外,王安忆还以温婉多情的智者情怀,或发现常识物象世界里的那些合规律合目的的审美物象的独立自存的诗意,如《长恨歌》里的波涛连绵的弄堂屋顶,精致细巧的老虎天窗,细雕细作的木框窗扇,细工细排的屋披上的瓦,细心细养的窗台上的月季花,具有葱绿桃红的光色之美的一衣一衫,给人色香味美感的一饭一蔬等;或对日常物象做移情化的审美,将这些常识性的物象提升为市民人生盛宴上的贴心贴肉的嘉宾,诗化为充满着人性的冷热温暖的与人心意相通的诗意物象。如《长恨歌》里窗边的后门是小姐和先生约会的私情通道;新式里弄的严密防范其实是欧美风范的民主防范,保护的是人的自由;即便是带着女人的阴沉之气的流言也不似故纸堆的流言那样冷淡刻板,而有着诚心与真情;每天从弄堂屋顶上飞向天空的鸽子则是城市情义绵绵的象征;茶、咖啡、香水、首饰、旗袍、照相馆、无轨电车等也大都有着一付与人贴肤贴肉共赴前程的模样;陷落于街头巷尾与飞短流长的城市有着一股宁屈不死的韧劲;喧腾的城市会发出柔软而揪心的哭泣。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如马丁·布伯所说,“由于我们的态度,我们会唤醒某物容光焕发而从其自然存在过程中〔转而〕接近我们。”[⑨]当王安忆将自己的诗意畅想与诗情体验泼洒在这个日常的物象空间时,日常实存的物象便从物质的自在存在跃升为“容光焕发”的审美存在;同时,对于人类来讲,人一旦与这些审美的日常物象相遇相伴,因日常生活的烦琐庸俗而带来的沉重感,因变动不定的人生而产生的迷茫与孤独便得到了有效的缓解与慰藉,继而产生日常生活的快乐体验和存在的确证感。由此,人也由日常的自在存在向审美存在飞升。有时王安忆还以外来人的视角,将日常物象濡染上一层神异的色彩。在《新加坡人》里,王安忆借新加坡人这样一个外来人的视角,移步换形,循着住宿-吃饭-消遣、消费-参观、旅游等路线,有层次地全面地展示了上海的饭店、餐馆、商场、里弄、街景等构成的都市物象世界。这些习以为常的物象在新加坡人的“惊奇”的审美中,敞开了其新奇的面目,饭店无奇不有;春节烟花流光溢彩中显出豪阔的手笔;蛤蜊面鲜美无比;欧陆乡村的房子呈现出仓圆屯满的气象;华美的卧室虽狎昵但因居家气息而抵消了猥亵;陈旧的里弄的对吵声如美妙的音乐;摩登的精品屋散发着一股幽秘的情调。海德格尔在《哲学何物?》中曾说过,“惊异是存在者的存在在其中敞开和为之敞开的一种心境。”[⑩]此即是说,“惊异是一种心境、心情、兴致,在这种心境、兴致中,‘存在’在‘存在者’、‘存在的东西’中敞开了,‘存在的东西’、‘存在者’由于‘存在’的敞开,而开窍了,而变得有意义了,而变得心花怒放了。”[⑪]正是在新加坡人惊奇、感叹、喜欢、感动等审美心境中,日常物象世界敞开了它的被日常态度所遮蔽的美丽的本然,人也由此被接纳到敞开了的存在中,获得人与物的存在契合的心花怒放的审美体验。
王尔德在分析审美化空间的社会意义时曾指出,“我们存在于它们之中犹如它们存在于我们之中一样。”[⑫]在王安忆所提供的审美的日常物象空间里,物象与人都互以主体的身份获得了诗意的再生与升华。
二、日常生活主体诗性品质的发现
王安忆最擅长塑造的市民日常生活主体形象是女性形象。究其原因,既因为王安忆的女
性身份,也源于王安忆对城市与女性关系的审美认识。她认为“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城市更适合于女性的生存,他们卸下了农业社会对体魄的苛刻要求,这个场所更多地接纳了女性的灵巧和智慧。”[⑬]这两段话昭示了王安忆对城市与女人、女人与城市的价值判断,她认为现代都市的诞生为女人的生存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和自由;女人才是城市的代表与英雄。
女人何以能成为城市的代表与英雄?王安忆依然从形而下的“过日子”的日常生活形态入手,展示女性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诗性品质,如生存品质、审美品质、生命品质与自由品质等。
(一)生存品质的审美发现。
“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⑭]王安忆正是从市民的凡俗人生里,了悟到海德格尔这一论断的深意,发现生存在存在中的重要意义。因此,她总是给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创设各种历史与个体生活的变故与遭遇,让她们在这种变故与遭遇之中去生存,在生存中显现她们的诗性品质。
《流逝》里的欧阳端丽,因“文革”暴风雨的袭击,从大家闺秀沦落至社会的底层。在此种历史与个体生活的大变故下,她不是选择逃避、堕落或愤世,而是选择了“去”生存,直面现实,放下小姐架子,织毛衣、带孩子、到街道工场工作,勤勉操持、精打细算一家人的日常生计,妥善处理家庭内外的日常交往,使风雨飘摇的一家人安稳地渡过了十年的动乱岁月,表现出力挽狂澜的生存的勇气、能力与智慧;《69届初中生》里的雯雯在经受了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艰难乱世的摔打考验和命运的百般作弄后,找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树立了“不管怎么,她要认真地生活......认认真真地好好儿地走下去吧”的务实的生存精神;《长恨歌》中的王绮瑶则表现出应对一切历史大变动和个体大灾难的沉着与从容。在经过撕心裂肺的伤痛和邬桥的身心疗养后,她理智地接受了李主任坠机而亡的不幸事实,沉着应对时代的大变迁,隐居平安里,靠给人打针养活自己养育女儿,从容安稳地渡过了贫穷动荡的50-70年代;《富萍》里的奶奶与吕凤仙在男人缺席的情况下,不慌不忙,靠帮佣过着衣食无忧舒心惬意的日子;富萍的婆婆新寡之后,带着残疾的儿子,打包、发货、敲砂模、拆纱头、运垃圾、倒马桶,从生存中不但练就了吃苦的本领和谋生的能力,也洇染上乐天平和的精神气韵;《新加坡人》里新的市井小民雅雯和小妹妹等虽然生在繁华的摩登时代,但也都谨守市民本分,“晓得有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人家的,不能有半点逾越,这才能神色泰然地看这世界无穷变幻的橱窗”;而老绅士则索性“老到底,放弃挣扎,就又有了一种风范”,老淑女们则“用心里的道理,规矩,藏着昔日时尚的教养。”总之,无论是对老市民还是新的市井小民,王安忆总是对她们怀抱理解之心,礼赞她们直面现实,应对变故,在任何艰难困境中都永远选择“去”生存的勇气、能力与智慧,礼赞她们坚韧顽强的精神,务实本分的品性,优雅从容的风度等。在王安忆看来,市民这衣食住行的日常生存因是人的存在的始基,又通向人的终极存在,因而这生存就“绝对不是苟活,不是动物性的本能,而是具有精神的攀高的意义。”[⑮]有着诗性的价值。
(二)日常生活审美意识与审美创造力的发现。
如许多美学家所揭示,审美能够唤醒人的爱欲、灵性、激情、想象,能够让人得到自由。王安忆承接张爱玲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写作传统,用温情的诗意笔墨描摹女性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意识与审美创造力。如果说,审美意识的主要特征是情感的话,那么,王安忆笔下女性的审美意识就不但表现为她们对日常生活的喜好、热爱与沉醉的感情或意志,也表现为她们从中所获得的愉悦的审美享受,包括激荡的生命感受、强烈的精神满足感,以及自由的想象与创造的乐趣等。
在《长恨歌》里,围绕着参选“上海小姐”这一事件,王安忆用热烈欢快的语调描摹了一幅“群芳争妍”的美丽图画:
“这一天就更是不同凡响。是小姐们的节日,太阳都是为她们升起的,照着她们从千家万户走出来。花店里的花是为她们罄售一空的,为的是庆贺她们入围。最漂亮的时装穿在她们身上,最高超的化妆术体现在她们脸上,还有最摩登的发型,做在她们头上。这就像是一次女性服饰大博览,她们是模特儿。她们的容貌是百里挑一。她们分开来看,个个可以夺魁;对比着看,一个赛一个,再要联合起来,这美便是排山倒海之势。她们是这城市的精髓,灵魂一样的。平常的日子里,她们的美洇染在空气里,平均分布的,而今天是特别的日子,她们集起精华,钟灵毓秀,画下这城市最美的图画。”
初升的太阳,美丽的鲜花,摩登的发型,漂亮的时装,高超的化妆术与娇美的容貌共同烘托出女性的美丽,女人就是美的化身!城市也因这美丽的女性存在而钟灵毓秀。最重要的是市民们也有着极强的审美意识,他们正从日常烦扰的欲求境界中抽身而出,为这美丽的女性奉上悉心悉意的红、白康乃馨,与美丽的城市一同沉醉在眩晕的无欲求的审美境界中。
不但如此,王安忆笔下的女性还是生活美学的身体力行者,对日常生活有着极强的审美创造力。即便是在美和生活情趣严重匮乏的“文革”,你也能从欧阳端丽、妙妙、雯雯、王绮瑶、严师母、郁晓秋等人对穿扮的添置改造,对吃食的精雕细琢上,感受到女性对日常生活美的天然感悟力、想象力与创造力,感受到她们实践吃饭穿衣戴帽的生活美学,传播着实事求是的人生意义的热情与不屈不饶。
由于王安忆笔下的女性常集美、审美意识与审美创造力于一身,因此她们就大都具有一种热爱世俗生活的美丽的情态或意态。如在《富萍》里王安忆描摹吕凤仙端着金碗慢慢地吃饭,打开账本细细算帐的意态,拉上钱包感觉富足、安宁、自豪的情态,简直就像一幅简约美丽的图画,在这幅图画里,王安忆聚集的是普通女性身上的那种精细的生活艺术、优雅的生活情怀和素朴的生活认识。《长恨歌》里的王绮瑶更是一个集情、意、趣、美于一身的女性。无论时局如何的风雨飘摇,她总是尽情发挥着女性生活的天份和创造力,悉心经营着一日三餐穿衣戴帽,做色泽美丽清爽可口的饭菜、精美淡香的点心,不断翻晒雅致华美的昔日时装,巧妙地修饰装扮自己,聚三五趣味相投的朋友,吃食、品茗、游戏、闲聊、逗趣,品味精致优雅的人生快乐,感受温馨暖融的人间情感,感悟平淡、细腻、踏实、本真的日常人生哲学。在平安里这个美轮美奂的世外桃源仙境里,王绮瑶不但因乱世而生的压抑与恐慌的身心体验得到了缓解,生活的兴趣被激发,而且生命与生存的趣味、意味与本真也被敞开被澄明。
(三)生命之美的发现。
人既是宇宙间最美丽的生命现象,如莎士比亚所礼赞的那样,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人同时又是宇宙间最充满悖论的生命现象,如帕斯卡尔所揭示的那样,人是如此孱弱渺小,以致一滴水都可以将他杀死。但是人又是如此的高贵,因为人有意识会思考,借助思考人可以通向无限与永恒。当然,王安忆对普通市民的生命并不作上述那样的形而上的思考,她只是站在普通市民的立场上,从日常生活视域切入去表现,因而她的书写就更多地表现出烟火人气的感性与平实。《流水三十章》和《逃之夭夭》这两个小说都以女性从襁褓之中到而立之年的生命成长轨迹为基本结构,共同思考仁慈、悲悯、爱与生命的快乐、幸福的关系。《流水三十章》探讨的是“爱”与生命成长的关系。张达玲自小缺乏血缘亲情的滋养,一生坎坷,命运滞塞不畅,生命黯淡无华,扭曲畸形。后来在皇浦秋的爱情感化下,张达玲开始感悟并实践人生最基本的“爱”,开始寻找生命的快乐感觉与和美状态。到了《逃之夭夭》,王安忆强化了《流水三十章》所表达的“爱”是生命之美的温床的这一思想,用诗意的语言,赞美在健康的市民社会里成长起来的健康的生命。和张达玲一样,因为私生女的身份与生不逢时的境遇,郁晓秋从小到大也没有目睹过什么幸福,但因为她天性热情和暖、择善而行、知足自乐,真率自然,所以,她也能欢欢喜喜地长大,快快乐乐地渡过如“新剥珍珠豆蔻仁”般热情、快乐的童年,如“千朵万朵压枝低”般青春花发的少年。即便是下乡插队,她也依然能将艰苦的生活过得如“豆棚篱落野花妖”般的充实与自然。最后,在返城的劳作、恋爱与婚姻生活中,她用自己的善良、悲悯与爱意谱写了最动人的生命华章:姐姐死后,她出于对刚出生就失去母亲的小外甥的怜惜,对双方风烛残年的父母的爱怜,对遭遇丧妻的姐夫的悲恸心境的体恤,对已故姐姐的怀念,接受了双方父母的意愿,选择和姐夫结婚,用自己的万千的爱意――母子之爱,母女之爱,夫妻之爱,姊妹之爱换来了生命的快乐与幸福,不但赢得了外甥、公婆、母亲的爱,也与丈夫结下了千肠百结、地老天荒的亲密感情。最后,经过生育磨难后的郁晓秋,活跃的生命特质经由体外潜进体内,完全化育成一个朴实、健康、成熟、美丽的女性:
“就像花,尽力绽放后,花瓣落下,结成果子。外部平息了灿烂的景象,留于平常,内部则在充满,充满,充满,再以一种另外的肉眼不可见的形式,向外散布,惠及她的周围。”
郁晓秋所以能在乱世和冷漠下健康快乐地生活,除却个人天性因素外,也与市民社会的健康与宽容有关,“她的身世之谜虽然是公开的秘密,人人皆知,但事实上,她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严重的歧视,她自己,也没有因此觉着比别人不幸。在拥簇杂芜的市民堆里,其实藏着许多开放的空隙,供某种常规之外的因素存身。”
王安忆在发现市民生命之美的同时,又何尝不是对能培育健康快乐生命的市民社会之美的再发现呢!
(四)女性自我意识与自由精神的审美发现。
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的特性就在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的自觉活动。”[⑯]海德格尔也说过,“此在”具有“向来我属”的性质,即“这个存在者在其存在中对之有所作为的那个存在,总是我的存在。”[⑰]换句话说,人之所“是”或人之“应然”就应该是自我的生成、设定与建构,是自由的实现与获得。尽管,在上述对女性的生存能力、审美创造力与生命活力的分析中,女性的自我与自由精神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显现,但是更深层的自我意识与自由精神还隐藏在王安忆对“城市与女人”的总体设计中。如前所言,王安忆把女性当作城市的代表与英雄,让一个个美丽的女性成为都市生活的主角,成为沉浮在都市生活大漩涡中的英雄。这种总体设计,就已清晰地昭示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与自由精神。米卡·娜佳曾说过,在19世纪的父权城市神话中,女人的城市地位是受到控制的,仅有的都市女人也被强加上种种不良的道德,“妓女和女艺人被描绘成城市风景图中的典型女性角色,以这种方式支撑着19世纪关于贞洁和堕落女人的二元想象,同样,也以这种方式支撑着有关性感放荡的城市之神话,与此同时,这些描述忽视了普通妇女。”[⑱]王安忆正是在都市女性对自我缺席的历史与道德关系的修改中,敏锐地发现了女性群体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精神的觉醒。此外,在“城市与女人”的总体框架内,王安忆让她笔下的那些美丽女性快乐地出入日常公共空间,参与公共活动。如活跃在《长恨歌》里的女性,无论是四十年代的王绮瑶、蒋丽莉、吴佩珍还是七八十年代的薇薇、张永红等,她们拒绝固守狭小的家庭私人空间,大胆地涉足公共世界,自由地穿梭在大街小巷,穿梭在城市向她们开放的各种公共区域,如片场、照相馆、舞场、茶室、咖啡厅、百货公司、购物广场等,她们快乐的身影还出入在各种日常公共社交活动中,如演戏、派推、选美、应酬等。特别是当她们与新款商品――时装和家居商品相遇时,她们决定着买什么不买什么,这时她们就成了时尚口味的权威,新事物的阐释者。威廉·李奇在对美国百货公司进行研究后得出如下结论:“在消费资本主义那些早期......令人愉快的日子里,逛百货公司构成了其大部分内容,许多女性认为她们发现了一个更让人激动的......生活。她们对消费体验的参与和挑战推翻了传统上被认为是女性特征的复杂特质――依赖、被动......家庭内向和性的纯洁。大众消费文化给女性重新定义了性别,并开拓出一个和男性相似的个性表达的空间。”[⑲]事实上,女性正是在城市的公共空间里挑战了传统的性别习俗,完成了女性自我和女性自由的表达。《富萍》里的富萍在都市文明生活的召唤下,担着背信弃义的道德骂名,毅然放弃乡下的婚约,选择从乡入城的道路。这既展示了城市对一个乡下女孩的宽容接纳与心悦诚服的“征服”,也展示了城市中的女性从被动生存到主动生存的自我觉醒历程。正是在自我觉醒的意义上,富萍沉默的个性实际上是女性自我筹划自己未来,追求自由生活的坚定;富萍的执拗性格也可当作是她不容别人对自己自由选择权利的侵犯。
三、市民日常观念世界的审美发现
对日常物象世界和日常生活主体的诗性发现,似乎还难以使王安忆释怀。于是,王安忆便潜入市民日常生活更为深层的观念世界,借助理性的阐释话语揭示了市民日常观念里所蕴藏的诗意。
首先是揭示日常生活抽象观念的“真”。
在《我爱比尔》里,王安忆借马丁和阿三之口道出“本来”与“存在”,“本来”“就是我的手摸得着的,而不是别人告诉我的”,“手摸得着的是我们人的本来,想象的是上帝的本来”;“事情发生了,就存在了,存在就是合理”。此即是说,王安忆认同的“本体”与“存在”是一个经验界或现象界里可触摸可感知的现存的实在或实有。在这样一种本体观、存在观的导引下,王安忆还诠释了“历史”、“政治”与“女性”等概念。比如“活着”,王安忆认为“活着”就是城市里一股压抑着的心声,城市那些喧腾的声音尽管淹没了它,“但其实它是在的,不可抹杀,它是那喧腾的底蕴,没了它,这喧腾便是一声空响”(《长恨歌》),换句话说,“活着”是城市的“芯子”和底蕴,或者说,城市的“本来”是以日常为其面目的。进而论之,王安忆认为历史与政治的“本来”也是以不变的“活着”为其面目的,“王绮瑶不知道,那大世界如许多的惊变,都是被这小世界的不变衬托起的”(《长恨歌》);“上海的市民,都是把人生往小处做的。对于政治,都是边缘人。你再对他们说,共产党就是人民政府,他们也还是敬而远之,是自卑自谦,也是有些妄自尊大,觉得他们才是城市的真正主人”(《长恨歌》),不管星移斗转,不管改朝换代,人总是要过日子的,与政治历史风云相比,“过日子”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此外,基于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位置,王安忆甚至将女性作为城市的标记或象征,“上海的繁华其实是女性风采的,风里传来的是女用的香水味,橱窗里的陈列,女装比男装多。那法国梧桐的树影是女性化的,院子里夹竹桃丁香花,也是女性的象征。梅雨季节潮黏的风,是女人在撒小性子,叽叽哝哝的沪语,也是专供女人说体己话的。这城市本身就像是个大女人似的,羽衣霓裳,天空撒金撒银,五彩云是飞上天的女人的衣袂。”(《长恨歌)
事实上,王安忆的这些发现,正是人类存在之所是,也已被人类历史发展所反复证明,如海德格尔所说:“所有艺术作为让其所是的真理出现的产生,在本质上是诗意的”,[⑳]由此,我们说王安忆的这一发现是诗性的发现。
其次,王安忆还从习焉不察的日常观念中,发现了它们所可能隐藏着的情趣、意味与诗意。比如“平常心”,《长恨歌》里的老克腊认为,“那真正为主的却不动声色,也很简单,甚至相当朴素,是一颗平常心”,超凡脱俗的罗曼蒂克与简单朴素的“平常心”的区别,就像巴黎的香水味和白兰花的气息的不同,“前者是高贵,后者是小户人家的平实,带点俗气,也是罗曼蒂克之一种,都是精心种植再收获的。前者虽是有着超凡脱俗的想头,行起来还是脚踏实地。这是人间烟火的罗曼蒂克,所以挺经久耐磨,壳剥落了,还剩个芯子。”又如对“从俗入流的心”、“耐心”、“名利心”、“虚荣心”、“好看”等观念,王安忆在《长恨歌》里也都有诸多新见,“不要小看这些从俗入流的心,这心才是平常心,日日夜夜其实是由它们支撑着,这城市的繁华景色也是由它们撑持着。这些平常心是最审时度势,心眼明亮,所以也是永远不灭,常青树一样”;“耐心是百折不挠的东西,无论于得于失,都是最有用的.....无论是成或败,耐心总是没有错的,是最少牺牲的”;“上海的小姐就是与众不同,她们和她们的父兄一样,渴望出人头地,有着名利心......上海这城市的繁华起码有一半是靠了她们的名利心,倘若没有这名利心,这城市有一半以上的店铺是要倒闭的”;“都说那心是虚荣心,你倒虚荣虚荣看,倘不是底下有着坚强的支撑,那富丽堂皇的表面,又何以依存?”“恩和义就是受苦受罪,情和爱才是快活;恩和义是共患难的,情和爱是同享福的”;“小姊妹情谊是真心对真心,虽然真心也是平淡的真心”;“照片上的王绮瑶,不是美,而是好看。美是凛然的东西,有拒绝的意思,还有打击的意思;好看确是温和的,厚道的,还有一点善解的。她看起来真叫舒服。她看起来还真叫亲切,能叫得出名字似的”。如此等等,这些阐释一经注入王安忆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宽容、温情与悲悯的理解,也脱离了既往的凡俗与平庸,闪烁着温婉感人的情趣与意味。
到此为止,我们从日常物象世界、日常生活主体精神品质以及日常观念世界三个层面,由浅入深地揭示了王安忆对市民日常生活世界的诗性发现。这些诗性发现就像一部诗化了的市民日常人生哲学:这既表现在王安忆打破了日常生活世界和终极的意义世界之间壁垒深严的格局,发现了被宏大叙事与启蒙话语所遮蔽了的合乎理性,合乎规律,合乎必然性的日常生活真理,揭示了形下的日常生活恰恰是人类得以存在的本体和根基,具有终极的意义,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1]也即是说,虽然王安忆写的是“现存的”庸俗与琐碎的日常生活,却具有黑格尔所说的“现实的”形上的理性品格――“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同时也表现在王安忆为避形上表达的虚空与虚无,又总是将哲学表达与感性诗学紧密结合,用市民的普通情怀去体验、感悟与理解日常生活,用温情的审美的目光去发现日常生活世界的动人诗质,如日常物象世界的“物性”与市民的诗性品质等。哲学化与移情化、审美化双管齐下,从而使王安忆对市民日常生活世界的书写布满了细腻的温情,温婉的善意,散发着优雅温馨的审美情调,蕴藏着素朴深刻的哲理。概括之,王安忆笔下的市民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真、善、美与知、情、意相统一的诗性世界。
然而,诚如郜元宝先生所说,优秀的长篇小说家在气质上都很痴迷,很偏激,很固执。王安忆在诗化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同时,也表现出对上海市井文化的过分痴迷。这无疑会妨碍她对市井文化局限的理智审视,也不利于她对上海市民的狡猾、脆弱、算计、冷漠、逃避、物化等缺点进行清醒的反思。在王安忆的小说里,不难看到她对一些流俗的日常观念的津津乐道,比如,“衣服也是一张文凭.....衣服至少是女人的文凭”(《长恨歌》),“只要把眼前过去,就是个长久之计”(《长恨歌》);“女人最重要的其实是两件事情,一是身材,二是皮肤”(《流水三十章》);“要说做人,最是体现在穿衣上的,它是做人的兴趣和精神,是最要紧的”(《长恨歌》)。正是这些局限使王安忆的写作难免染上一些庸俗之气。但是,瑕不掩瑜,无论如何,王安忆对市民日常生活的诗性发现,为日常生活和日常观念的正名,其文化意义美学意义、性别意义都是十分重大的。
注释:
[①]转引自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11月版,第96页。
[②]刘成纪:《物象美学》,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6页。
[③]刘成纪:《物象美学》,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279页。
[④]刘成纪:《物象美学》,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279页。
[⑤]有关海德格尔的“物”与“物性”理论,参看海德格尔的《诗·语言·思》中“V物”的论述,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2月版。
[⑥]王安忆:《忧伤的年代》,见王安忆《伤心太平洋》(中国小说50强1978年-2000年),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397页。
[⑦]王安忆:《忧伤的年代》,见王安忆《伤心太平洋》(中国小说50强1978年-2000年),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403页。
[⑧]王安忆:《忧伤的年代》,见王安忆《伤心太平洋》(中国小说50强1978年-2000年),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10版,第401页。
[⑨]转引自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371页。
[⑩]转引自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229页。
[⑪]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229页。
[⑫]转引自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128页。
[⑬]王安忆:《上海的女性》,海上文坛,1995年第9期。
[⑭]〔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2006年4月版,第49页。
[⑮]王安忆:《柔软的腹地》,小说选刊,1998年第12期。
[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⑰]〔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三联书店2006年4月版第50页。
[⑱]米卡·娜佳:《现代性拒不承认的:女性、城市和百货公司》,见《消费文化读本》第170页,罗钢,王中忱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
[⑲]转引自米卡·娜佳:《现代性拒不承认的:女性、城市和百货公司》,见《消费文化读本》第191页,罗钢,王中忱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
[⑳]海德格尔著,彭富春译:《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6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