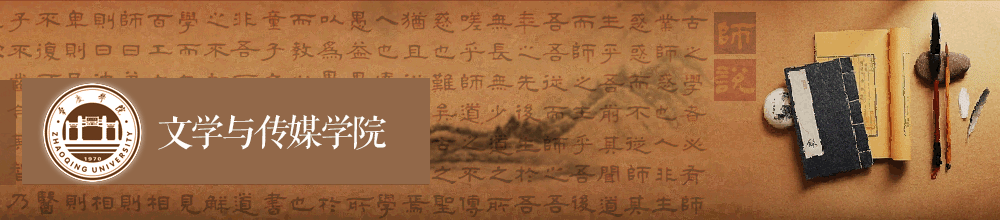[提要]中国新诗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是其都市话语质性。20世纪中国新诗都市话语价值取向在历史和逻辑的层面上表现为理想化、感伤化、批判化和世俗化的态度。而在这些价值取向中,由于乡村他者的过滤、中介,形成中国新诗都市话语的特质与困境。
[关键词] 都市话语 价值分析 乡村他者 矛盾困境
都市是现代工业文明的重要表征,现代化过程必然地遭遇都市化问题。20世纪中国新诗是在都市背景下展开的,它的诸多特征及其困境都可归结于都市的生存方式、视觉图景及其价值取向。本文试图从现代诗人对待都市的态度入手,揭示20世纪中国新诗从古典向现代转化的艰难历程。
一、中国新诗都市话语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诗歌史上最早和现代都市发生关系的是清代士大夫们在国外的游历,在黄遵宪周游各国的纪行中,西方的事物和话语开始进入他的诗作中。在《今别离》诗中,出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标志性事物如轮船、火车、电报和照相术等。他在《香港感怀》中,对香港的工业化的印象是“弹指楼台现,飞来何处峰”,“火树银花耀,毡衣锈缕铺。”然而,这些表现局限于感知表象,仍没有突破古典诗歌的感兴模式。真正意义上具有现代都市特质的诗歌是从郭沫若的《女神》开始。朱湘认为《女神》的特点是“在题材上能取材于现代文明”①。闻一多先生则认为《女神》中的“动”与“力”最能代表现代性和时代精神,成为“近代文学一切的事业之母”,“近代文学之细胞核”②。在《笔立山头展望》一诗里,郭沫若情不自禁地表达了对现代工业的礼赞,他把工厂的烟囱看成是“黑色的牡丹”,“二十世纪的名花”。郭沫若在一种情绪化的话语中,肯定工业文明的合理合法,无疑给20世纪中国新诗的发展提出了一种新的指向。综观五四时期的诗人心理,现代化观念被普遍接受,工业化被看成是救国的主要路径之一。在此语境下,都市话语更多地表现为观念性的反映。虽然五四时期的诗人很少表现现代都市的感性体验和对都市存在的本质性反思,但它为中国新诗都市话语的展开提供了观念上的准备。郭沫若的诗作被当时的人们评价为时代精神的代表,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普遍心态。
五四时期的诗人大部分虽生活在北平、上海等都市,但他们更多地沉浸在个人的情感和思想上,表现为自我的抒情和简单的说理。早期新月诗人则更多地倾向于对理想和自由的浪漫抒唱。在二十年代中后期,部分诗人开始在都市里以流浪者的身份感伤失去的乡村家园,愤慨都市的无情与冷漠。艾青在《马赛》、《巴黎》中对都市的态度具有代表性。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都市的财富和繁荣令诗人向往;另一方面,诗人又站在东方的角度给予批判与否弃。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首诗里,有一个意象“妓女”反复出现,成了都市的隐喻。如
巴黎/解散了绯红的衣裤/赤裸着一片鲜美的肉/任性的淫荡
巴黎/你患了歇斯底里的美丽的妓女
巴黎,你—-噫/这淫荡的/淫荡的/妖艳的姑娘 (《巴黎》)
这种都市——妓女的象征模式蕴含着20世纪中国新诗对于都市的双重情感,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何其芳在《云》中写到:“我走到海边的都市。/在冬天的柏油的街上/一排排的别墅站立着/象站立在街上的现代妓女,/等待着夏天的欢笑/和大腹贾的荒淫、无耻。”王统照在《她的生命》中描写的都市是“织着迷荡的色丝,包藏着娇媚的骷髅”。吕亮耕在《都市的文明在哪儿》诗中把“伸展的道路”比作“荡妇的胸怀”,胡拓在《夜底葬曲》中形容都市的夜“仿佛一个妖艳的淫妇/以诱惑的姿态淫荡地迷糊着人呵/让人们沉湎于她的秽亵的怀抱/——夜是淫奔而迷惑的呀。”都市被看成恶的存在,在二三十年代诗人中最为普遍。李金发是最为认真地对待这一问题的诗人,他的诗作大部分都是留法时期创作的,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对他影响深刻。金丝燕博士概括地认为:“对波特莱尔的接受,使李金发成为第一位中国的‘恶魔诗人’。他经历精神的失望,……体验着颓废的反常与精美的滋味。”③。腐尸、枯骨、恶臭、魔鬼、深渊这些充满波特莱尔式的“异国情调”的意象是李金发对都市的感觉。恶的迷恋和诅咒同时并存,都市被看成是“鬼魅”和“天使”的混合体(《忆上海》)。与李金发有同样感觉的是王独清、于赓虞、胡也频等诗人,他们都表现了对于“都市生活之颓废的享乐的陶醉与悲哀”④。追求感官的刺激和灵魂的救赎企图形成象征派诗歌独特的精神现象。在他们的话语中充斥着酒色与咖啡,疲乏、感伤和颓废,形成都市生命的质性。
二三十年代中国新诗对都市的感知主要表现在个体的生存体验上,具有浓厚的情绪化感伤成分。走出了封建家园的诗人们在获得了自由的同时发现自己一无所依,不得不独自面对整个社会。生存的艰辛和沉重的承担造成诗人们精神上巨大的压迫。诗人朱湘由于生计的艰难和人际关系的紧张而跳江自杀便是现代生存的悲剧性事件。现代诗人生活在都市而被都市所拒绝,这种游离于都市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与
都市的距离,从而以流浪者的身份参与都市的生活。他们沉溺于都市的酒色奢靡生活,感伤生命的虚无
与幻灭,在颓废中自叹自恋,从而避缩回自己的情绪中营造诗的象牙塔。
四十年代的穆旦,为中国新诗都市话语的价值取向提供了新的维度。由于理性话语的介入,都市图景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揭示。隐藏在都市的朦胧面纱背后的是生存的严酷性,现代官僚体制,职业化分工的运作机制,技术化工具理性这些现代性因素不可抗拒地物化生命的自主性。在穆旦诗中,人全面地成为都市的奴隶,匍匐在“钢筋铁骨的神”的脚下。都市
把我们这样切,那样切,等一会就磨成同一颜色的细粉,/死去了不同意的个体,和泥土里的生命;/阳光水份和智慧已不再能够滋养,使我们生长的/是写字间或服装上的努力,是一步挨一步的名义和头衔,/想着一条大街的思想,或者它灿烂整齐的空洞。(《城市的舞》)
世界的主宰让位于物的专制。诗人关注着个体的自主自由丧失的无名性。都市生存条件下生命的异化构成思的主要对象。自然、纯真、质朴随着乡村社会的消解而一去不返。都市里的人性沦丧与理性——懦弱的等值成为生存的严重事件。“送人上车,掉回头来背弃了动人的真诚”(《智慧的来临》),诗人为普在的阴谋、欺骗、狡诈而痛心。成熟意味着童真的丧失,在“不败的英雄,有一条软骨”(《鼠穴》)中,良知无奈地泯灭。穆旦在痛苦与焦灼中揭示出都市生命的庸俗、无意义。四十年代的诗人中,袁水拍、杜运燮、袁可嘉等的创作都对都市人生给予讽刺和鞭挞。理性的辨证分析是四十年代都市诗歌的特色,反讽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修辞策略。四十年代新诗的都市话语和西方存在主义思潮有着相通之处,都市从本质上显示了恶魔般的品行,它以异化物化形式使生命失去了完整性和自主性。四十年代诗人对都市的态度是批判与否定的,他们从两个角度切入都市话语,一个是政治层面的,政治的黑暗与腐败是造成都市生存堕落的主要原因;另一个是文化层面的,都市的工商文化所强调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性直接颠覆了世代恪守的传统伦理。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在诗歌文本中不断地被消解,都市生活的日常性成为诗歌话语的中心。在后朦胧诗人的作品中,一种相异于精英文化的市民意识得到了表现。“真实的生活在河这边/在等待火车开过的栅栏前/每一张脸都反映出集体的冷漠//真实的生活在自由市场的喧闹中/在一颗白菜放进称盘的时候//在河这边,真实的生活/是葱姜奶奶和花草爷爷的对话”。这是王小龙的《真实的生活》中的几个片断。生活的真实性就在此岸的平淡忙乱中,此在的现实性不再被置疑。在后朦胧诗人中,“诗歌精神已经不在那些英雄式的传奇冒险,史诗般的人生阅历、流血争斗之中。诗歌已经到达那片隐藏在普通人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底下的个人心灵的大海。”⑤他们推崇对日常生活的感觉还原。如“我坐着/ 看着尘土的玻璃窗/ 心境如外面的天空/阴郁/或者晴和/没有第一个欲望/也没有其它的欲望/某个女朋友/她要出嫁了/另外一个/我很想最近去看看她/就这样/我的表情/一会阴郁/一会晴和/如外面的天空”(小君《日常生活》)。无思的生存合法化,只留下愿望的片断,自足的日常生活的心灵图景滞留于片刻的一念一觉之中。后朦胧诗人的诗歌话语全面关注都市生存的当下状态,他们对都市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们对都市人生的世俗性、现实性持肯定态度。残缺、庸俗和世故演绎着都市儿女的生命质性。感性享受与本能冲动的快感成为人生的终极辩护,日常生活的实在性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先权。个体的媚俗或放荡不羁是完全私人化事件。后朦胧诗人的反价值理论实际上是破除生命中彼岸性的存在虚幻,从而肯定此在的肉身。其次,面对都市生存的单向度,平面化,诗人没有乌托邦式的重构企图。生命简约为生活现象和状态。随着神性的解构,凡俗化的生存由诗学话语的边缘移向中心,娱乐和消遣作为凡俗人生的合理性不再产生罪责感。再次,都市生存的此在的荒诞和矛盾性构成人生戏剧的主景。人生的严肃性成为揶揄的对象,生活被看成是一种游戏。在后朦胧诗人的作品中,冷漠与孤僻奇异地结合在一起,在所谓的“零度写作”中,形成一种超然而又漠然的诗风。
当我们回顾20世纪中国新诗都市话语的价值取向时,我们发现:第一,汉语诗人对待都市的态度与中国社会历史的现代化进程是基本一致的,从理想化的礼赞、情绪化的感伤、理性化的批判到世俗化的肯定的逻辑发展和现实历史的发展脉络相吻合。虽然他们不是线形发展的,但其脉络仍隐约可辨。而且,诗人的肯定与否定大部分也只是针对都市的某一现象,中国新诗很少深入到都市的工业文明的本质——科学技术的层面进行反思和批判,大都是以生命的都市遭遇为切入点感知、思想,缺乏形而上的理性追问和重建存在的理论力度。由于20世纪中国社会处于封建的自然经济向都市化的工商经济转型的时期,而且这种转型还远没有完成,所以新诗的都市话语一直处于诗学理论的边缘。第二,中国现代诗人对待都市的态度既受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诗歌理念影响,又是他们根据现实的感受,主动选择的结果。中国现代诗人在走向都市化过程中过早地遭遇到西方的“世纪末”情绪和现代与后现代思潮,他们在进入都市过程中以先入之见来建构现实。他们对都市还没有认真地体验认识,便做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先行的现象在现代诗歌史上是普遍存在的。20世纪中国新诗的发展是在中西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展开的,他们对都市的感知具有全球化的色彩,大多数诗人都曾生活在国外的大都市里,对都市的感知也部分地源于国外生活。在诗歌理念上他们接受了西方现代诗歌的理论主张,从早期对象征主义的接受到目前的后现代思潮的盛行,整个诗学话语体系无不在西方思想中获得资源性的支持。第三,在这些价值取向中存在着诸多的矛盾与困境及其历史深层动因,它们制约着现代都市诗歌的丰富与发展,成为探讨20世纪中国新诗都市话语的价值取向的不可回避的命题。
二、乡村他者:中国新诗都市话语价值判断的支点
在20世纪中国新诗的都市话语中,存在着一个潜在的“他者”——传统的乡村文化形象。它渗透在诗歌文本中制约着诗人的价值取向。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现实中,乡村文化和都市文化的互动产生的张力构成都市诗歌话语的独特性。古典与现代的矛盾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冲突。由于中国新诗的主体运思方向是如何使新诗现代化,古典的文化价值沦落为新诗的“他者”形象,而“他者”的身位表明民族精神的基本原则悲剧性的失落。然而,民族性毕竟是诗人生存的土壤与背景,它从各个方面渗透在诗人的创作中,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参与新诗话语的建构,仍然是现代话语中的活性成分。
首先,乡村文化作为一种参照系,一个特定的视角,影响着中国新诗都市话语的建构。都市文化的生机活力相对于乡村的静谧安宁才能凸显,而都市的冷漠物化只有放在乡村的自然和谐的前提下才更触目惊心。中国早期都市诗人从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来到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对大机器生产、便利的交通、丰富的商品等生产力要素情不自禁地产生惊叹,这是两种文化碰撞的心理震惊。细究郭沫若、艾青等人的都市题材的诗歌,很少注重主体的个人形象,诗人隐逸在文本之外,缺乏具体的身份。诗人的抒情视角是局外旁观,因而诗的意象也是观念化和印象式的。正因为诗人的都市感性经验的缺乏,造成他们诗歌文本的都市质性的薄弱。
其次,以乡村社会的传统文化观念构成诗人都市生存中所眷念的精神家园。李金发一方面声称“‘牛羊下来’的生活,自非所好”(《故乡·序》),另一方面又试图超越都市生存中的“混乱”,“要把生活简单化,人类重复与自然接近”⑥。在他的诗里,有着深深的乡思和对简朴的向往。正是这种“怀着乡愁,寻找家园”的冲动,使得戴望舒、何其芳等诗人游荡在都市里,踯躅、苦闷、忧伤。乡土,已经失去,却不能忘怀;都市,已经进入,却不能认同。怀乡变成精神上的逃离,在古典诗性的遥望中,他们试图撑起生命深处的“油纸伞”,抵挡都市风雨的无常。千年古镇的梦中,“丁香姑娘”是一个永远的企求。戴望舒以都市的浪子的身份叩问精神漫游的意义,“这是幸福的云游呢,还是永恒的苦役?”(《乐园鸟》)都市里古典诗性的丧失,使三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变成一群现代的寻梦者。何其芳在古典的梦境中寻觅着朦胧神秘的美,企盼梦中的女神的来临。在这种都市失语症中,他们沉浸在晚唐五代诗词的脂香中,维系着生命的统一性。在中国现代诗人心中,古典文化的美学情韵蕴含着浓郁的诗性内涵,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情结。以自然的神性消解都市的魔性,现代诗人获得广泛的话语权,他们可以在自己精心构造的乡村神话中自在逍遥,超脱此在的凡俗性。
再次,在传统乡村文化中提炼的“自然”、“童真”、“野性”等观念在穆旦等人的诗里构成对现代都市的批判功能。穆旦在新诗史上的独特性在于他以辨证的态度来处理乡村与都市的关系,乡村的自然经济形式和封建政治形态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工商资本主义不可抗拒地获得统治地位,但传统文化中仍然有人类永恒价值的积淀,它是人性中重要组成成分,不应被忽视或践踏。穆旦在揭示都市生存的灰暗与无奈时,呼唤着一种生命的本真形式的重临,一种与泥土、大地亲密无间的存在来对抗世俗的侵入。乡村,虽然淡化为办公室的“壁上油画的远景”(《小镇一日》),但它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却成为诗人永恒坚持的信念。
最后,在后朦胧诗人的都市话语中,乡村图景与观念全面消隐。都市成为诗歌话语的中心。随着乡村话语的淡出,都市被随意散乱地处置,从而“放弃了超越现实的努力,对精神、价值、终极关怀、真理、美、善这些超越价值失去了兴趣,……不再区分真善美和假恶丑,不再作价值判断,在精神失控的状态下,沉醉于卑微愉悦的感官享受中”⑦。在乡村的价值理念的参照与中介缺失和新的市民理性尚未成熟的前提下,都市话语显示了从未有过的平面性,无深度感。后朦胧诗因之失去了“意义”的寻问和批判性的对社会现象透视。由于后朦胧诗人不再设想彼岸的神性存在,理想和现实、精神和肉体、神性和魔性的二元对立消失了。乡村他者的缺失使都市失去了与另一种文化对话的可能,从而也最终消弭了新诗都市话语的紧张感和戏剧化张力。后朦胧诗放逐了古典的诗意诗境,因而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诗学大厦。它的是非功过现在还远不是给予评定的时候,但它所进行的诗学革命可以说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彻底。
三、对中国新诗都市话语价值取向的反思
20世纪现代诗歌的都市话语历史性地表现为乡村“他者”由“在场”到“缺失”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反映了中国新诗的诗学观念的变迁,乡村与都市这一基本矛盾及其隐含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影响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在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都市化所代表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工业化所追求大机器生产和利润最大化的效率观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现代诗歌都市话语的价值取向隐含着社会结构转型期精神上的阵痛与困境。在物质层面上,诗人充分依附于都市的物质丰富性、便利性。而文化工业的发达又刺激、吸引着诗人云集都市以获取功名。在精神层面上,诗人们又深深地领悟到商品拜物教对生命的物化,人在获得财富的同时成为财富的奴隶,生命的一切生存要素被量化、标准化、形式化。乡村化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所必须逾越的对象,然而在乡愁的驱动下,他们又神往依恋于古典的乡村情韵。他们在精神上承接了古典的优雅和精致时,遗失了对都市存在的思。这种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断裂现象,表达了中国现代诗人维系话语中心的努力。穆旦诗歌的矛盾尤为典型,他以自然、童真、野性这些乡村文化的观念来批判都市生存的世俗性,从而获取反思都市存在的视界。因之,生命在堕落的不可免和救赎的不可能中注定成悲剧。一方面是乡村文化理念的神性,另一方面是都市生存的魔性,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构成诗歌文本的主体架构。然而我们需要追问,以自然、童真、野性的观念对工业化生产与商品化世界进行批判是否具有有效性、合法性,以一种文化理念过滤另一种文化现象是否具有逻辑的合理性!
后朦胧诗人放弃一切传统理念对都市现实的重构,“诗人不能忽视他面临的事实”(柏桦语)。在亲切、平实、生动的语感中,都市在一种“杂语喧哗”中再现了一种自在的世俗美。他们沉浸在语言的狂欢中,游戏人生,解构神圣,戏谑观念化的权力意识和形态化的精英话语。他们回归于都市的市民文化,也终止于市民无思的狂欢。然而,市民社会难道就真的如此轻松自如?责任和使命真的离他们而去?纯真、浪漫的情怀就不被人类所珍视?正如王岳川先生所言:“生命中确乎有不可承受之重,但别忘了,真正难以负荷的倒是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在我看来,这为杰姆逊称为零散化、平面化、复制化的世界,一切都可复制,一切都因复制而有备用品,然而,生命本身不可复制,爱情不可复制,母亲和孩子不可复制备用,对生命、爱情和世界意义的本真感悟同样不可复制备用。”⑧在解构的层次上,后朦胧诗宣告了用传统的文化观念和政治话语来阐释市民社会存在的无效性,但是,在建构的层次上,后朦胧诗人也同样没有提供一种话语来有效地阐释市民社会存在的理念。在后朦胧诗的语境上,传统价值的完整性、统一性已经不可回归,生命的意义正在凋零,虚假的乐观主义只是欺世盗名,当一切退回到零的起源时,我们如何面对?
注 释
①转引自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诗话》,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②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载《创造周报》第3号。
③金丝燕《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第26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④穆木天《王独清及其诗歌》,载《现代》第5卷第1期。
⑤于坚《诗歌精神的重建》,载《快餐馆里的冷风景》,第26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⑥李金发《复刊感兴》,载1931年《美育》第4期。
⑦赵祖模《中国后现代文学丛书·总序》, 载《快餐馆里的冷风景》,第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⑧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第4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本文原载《学术研究》200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