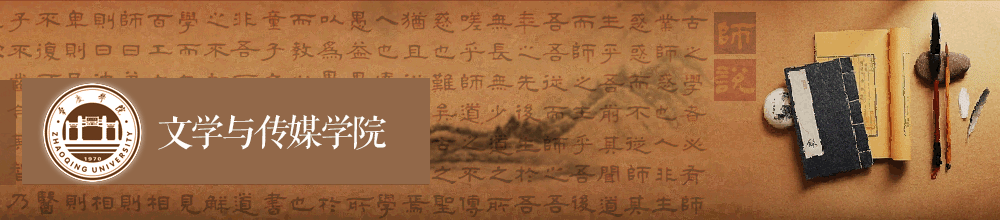——本文发表于《牡丹江大学学报》2012.4
李宝莹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08级(1)班 学号200824051137
摘要:张爱玲小说中塑造的“汽车”意象,真实和虚幻同在,传统和现代交替,是人物外在生存环境的暗示、人物内心世界的反映,更细致地折射出传统与现代交错的爱情观。总之,张爱玲在一部小小的汽车里,蕴藉着时代的变迁和人心从希望到绝望的变化,既美丽又凄怆。
关键词:张爱玲;汽车意象;爱情观;传统;现代;人生
意象本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一个美学概念。古人有所谓“立象以尽意”,反过来说,就是意中之象的意思,这个意思最初在先秦的哲学中出现,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才正式把意象引入文艺理论领域。张爱玲笔下的种种意象既是感性又是渗透着理性的,而且具有强烈鲜明的主观情感特色。她的作品中常常会用到月亮、太阳、镜子等传统意象,特别在她40年代的作品中,关于汽车(车、电车)意象的描写比比皆是。在长篇小说《十八春》(又名《半生缘》)中,对汽车的描写居然有七十三次之多[1]1--288,在《倾城之恋》里,对汽车的描写有十八次[2]46--88,小说《色戒》中汽车出现了五十三次[3]223--231,在短篇小说《茉莉香片》[1]88--111、《第一炉香》[1]111--164、《第二炉香》[1]164--201中,汽车也分别出现了五次、六次不等。而作品《封锁》[1]201--213描写的就是一个在电车上发生的故事。可见张爱玲对汽车意象的确情有独钟。她所描绘的汽车并不十分特别,但多处的出现都有深刻的内涵。
朱光潜先生曾在《朱光潜美学文集》中提出:“意象的孤立绝缘是美感经验的特征。在观赏的一刹那中,观赏者的意识只被一个完整而单纯的意象占住,微尘对于他便是大千;他忘记时光的飞驰,刹那对于他便是终古[4]167。”朱光潜先生这段话正是对张爱玲作品的最好诠释。张爱玲作品中对景物的勾勒的确是带有明显的情感色彩。在同样的车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发生了各种各样耐人寻味、扣人心弦的故事,正是作者妙笔巧书安排下来衬托人物的内心还有暗示着人物所处的环境,甚至预示着人物悲剧的结局,更深一层,作者对汽车的描写,显现了时代蜿蜒的变迁,描摹了传统和现代爱情观、物质观的朦胧画卷。
一、人物外在生存环境的暗示
汽车是一个可以给人遮风挡雨,代替辛苦步行的交通工具。人们并肩前行漫步人生路被“一脚油门”所代替。通过汽车的行驶而变换的外在场景,就好像是跟随作者的文字去领略四季的变幻。而且由于汽车多在行走,外在环境总在变化,汽车对故事的后续发展也多了几分伏笔的意味。虽然是同样的汽车,但在作者渲染的不同的环境里,汽车对于人物所处的生存环境起了更大的暗示作用。
张爱玲是如此具有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她总能从琐碎的生活片段里挖掘到司空见惯却发人深省的片段。譬如《封锁》,它首先是一个场景—电车遭遇封锁后,车上的一个场景。小说开篇描述:“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鳝,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鳝,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钉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后他也不发疯。”[2]201生活就像打盹儿,沉闷、无聊,“如果碰不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2]201电车突然不再像往常一样在正常的轨道上往前走了,那么冲出正常生活轨道之后,人会出现一些怎样的问题呢?华茂银行的会计师吕宗桢开始鼓起勇气向身边的吴翠远说话了,从只是聊聊,就开始了诉说,慢慢的,在停止行驶的电车里,这个与外界隔绝的容器,令他一发不可收拾地堕入“情网”,说着说着,恋爱之感油然而生,断定了翠远“是一个可爱的女人——白,稀薄,温热,像冬天里你自己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2]209想到了他们的结合会牺牲了她的前程。可是终究,“封锁开放了。‘丁零零零零零’摇着铃”,[2]209吕宗桢回到了家里,而电车上那个女人的脸已经开始模糊,残存的印象只有自己胡言乱语的一些话。故事背景的变化从压抑到开放对应着越轨与回归。深层次地暗含着人们扭曲的心灵之中有形无形的压抑挣扎以及有意无意的封锁隔阂,个体常态受人生压抑而显现出非常态的变化。电车的外部是死静的,电车内却有些嘈杂,就在这既死静又嘈杂的背景下,徐徐展开了吕宗桢和吴翠远的、短暂的“爱情故事”。《封锁》里描写的“电车”是真实的上海,真实的租界的反映。人们的常态欲望是如何在这个非常态的环境中存在的呢——张爱玲偏偏就觉得人的欲望能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得到生长。在被封锁的有轨电车上,时间和空间瞬间停滞,封锁在无形中就为人们心里隐秘欲望的无限增长提供了养分。电车象征了真实的人性世界,以现实中的一次封锁为人们内心得以真正自由提供了可能,这是独属于张爱玲的真实——一个中西文明交汇,古今思想繁杂的上海。
又如《倾城之恋》中,“那车驰出了闹市,翻山越岭,走了多时,一路只见黄土崖,红土崖,土崖缺口处露出森森绿树,露出蓝绿色的海。到了浅水湾,一样是土崖与丛林,却渐渐明媚起来。许多游了山回来的人,乘车掠过他们的车,一汽车一汽车载满了花,风里吹落了凌乱的笑声。”[2]60这里的汽车简直如放映机一般,将范柳原和白流苏一同前行所处的环境以及日后故事的曲折发展都表现出来。名门望族的包袱和家人尖酸刻薄的言语令白流苏不堪重负,将自己“推销”给花花公子范柳原。她用自己的前途做赌注,“如果她输了,她声名扫地,没有资格做五个孩子的后母。如果赌赢了,她可以得到家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出净她胸中这一口气。”[2]59这一次坐上汽车,就是白流苏“赌博”之旅的开始。白流苏虽然对未来毫无把握,但无可否认的是,此时此刻的她是愉悦的,因此前景“渐渐明媚起来”。[2]60最耐人寻味的还是他们的车被一趟趟载满鲜花、充满欢声笑语的游山归来者的公共汽车掠过的画面,既是日常极普通不过的场景描写,却透露出淡淡的苍凉,象征着白流苏稍纵即逝的快乐,仿佛暗示着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场千辛万苦的倾城之恋正式拉开序幕。
香港沦陷后,载着范柳原和白流苏的卡车“在‘吱呦呃呃……’的流弹网里到了浅水湾。”[2]82停战了,他们沿着满是炸裂的石子的坑一路向前。“柳原与流苏很少说话。从前他们坐一截子汽车,也有一席话,现在走上几十里的路,反而无话可说了。”[2]83汽车里的沉默极具穿透力地映射到他们现实的生存境地中,外在环境的动荡骚乱令他们过着如草芥般漂泊浮沉的日子。汽车在坎坷中行走,人也在荆棘中匍匐。在汽车里发生的故事总是这样细细碎碎又悲凉不已。沦陷前貌合神离的惺惺相惜,令他们还能用话语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琐屑;战争后同游过生死的他俩,没有言语,却极致地融入彼此生活。
车子一路向前,故事未完待续,那是汽车载不走的倾城之恋。
二、人物内心世界的反映
在文学创造中,表现人物个性和内心世界的最佳手段,就是让情感在艺术作品中以具象的方式呈现出来,再通过富有特色的意象对象化出来。张爱玲小说中的意象亦如是。
“薇龙正走着,背后开来一辆汽车,开到她跟前就停下了。薇龙认得是乔琪的车,正眼也不向他看,加紧了脚步向前走去,乔琪开着车缓缓地跟着,跟了好一截子……”[2]158这是张爱玲短篇小说《第一炉香》中的一个片段。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乔琪和纯洁而有个性的女学生葛薇龙上演的“车随人走”的戏码,薇龙走,车子走,薇龙停,车子停。薇龙连忙往前走去,乔琪的车却依旧停在那儿,不再往前。薇龙想要摆脱乔琪吗?显然不。她期待乔琪会趁她停下来时表白,但事实却没有。这里的车,根本就是主人公的心。作者用车子的亦步亦趋揭示了主角间爱情的拉锯战。她“爱”乔琪乔,但更是爱现下浮华的一部分,爱到不介意透支未来,享受赌爱的快感。“《第一炉香》解析的是女人(乃至人性中)更普遍的弱点,所有在抽象层面,显示了人受虚荣、情感支配无法解脱,在历史层面,则表达了对都会小市民(尤其是女人)生态、心态的理解和同情。” [5]其实葛薇龙和乔琪乔,或是姑妈,底子是一样的。但是,乔琪和姑妈毫不掩饰的追逐着声色犬马,而葛薇龙却囿于自我的愧疚和负罪感,之所以那样执着于与乔琪的婚姻,于她而言,更意味着某个自欺欺人的平衡点吧。“张爱玲的譬喻充满了真正的女性意识,象一个冷静的敏锐的旁观者不经意的述说。” [6]132
“车过了湾仔,花炮啪啦啪啦炸裂的爆响渐渐低下去了,街头的红绿灯,一个赶一个,在车前的玻璃里一溜就黯然灭去。汽车驶入一带黑沉沉的街衢。”[2]60薇龙的人生何尝不是一片黑暗呢?由中学生到交际花,她在肮脏的环境中毁了自己,更在自身的欲望中毁了自己。车如人心,看遍了灯红酒绿的庸俗不堪,在一片黑暗中看清自己的悲剧,清醒,却无能为力。
《第二炉香》男主人公罗杰安白登“开着汽车横冲直撞,他的驾驶法简直不合一个四十岁的大学教授的身份,可是他深信他绝对不会出乱子,他有一种安全感”。 [2]165但故事中轻描淡写地提到这样的驾驶方法与罗杰的身份不符合,似乎又通过他这种“深信的安全感” [2]165去暗示着这正是他危机四伏,四面楚歌的时候。为后文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奠定了基础——他那个最美丽的妻子——愫细,因为没有受过性教育,在新婚之夜逃了出去,让罗杰丢尽了脸,从此在学校里抬不起头,并最终自杀。
《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是一个具有病态心理的精神残废的青年。他说他“顶恨在公共汽车上碰见熟人,因为车子轰隆轰隆地开着,他实在没法听见他们说话。”[2]88其实他根本不是讨厌在公共汽车上碰见熟人,而是厌恶熟人。这里的公共汽车就如聂传庆拥挤得快要膨胀的心脏,颠簸中失去自我。摇晃的不仅是车,还有他苍白的心。他认为自己错误的生命源于母亲的怯懦,他对自己的父亲彻底地冷漠。在无法说明的难受中,他迁怒于夺走自己父亲的言丹朱——言子夜的女儿,也就是在公共汽车上遇见的那个“熟人”,他心上的那个“熟人”。对聂传庆来说,言丹朱是他梦寐以求的形象的化身;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仇恨,而言丹珠就是现实中引爆他仇恨的导火线。他憎恨这个美妙少女在学校里给他的一切温柔,却又无法摆脱言丹朱给他亲近的诱惑,于是,他的精神陷入了病态……
细细体会张爱玲的作品,愈看愈无法摆脱她字里行间那沉重的枷锁。犀利的文字拼凑成一袭袭华丽又肮脏的衣袍——那叫现实。
三、传统与现代的爱情观
张爱玲所塑造的人物的爱情观,又或者说那根本是张爱玲自己的爱情观,相对现在而言可能是传统的,但相对当时而言是超前的。正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在恍惚中独自站在人行道上,瞪着眼看人,人也瞪着眼看她,隔着雨淋淋的车窗,隔着一层层无形的玻璃罩——无数的陌生人。你在车里,我在车外,已是恍如隔世。车,仿佛是一块隔开一个时代的玻璃,传统和现代互相对望,明明有相似之处却互不相识。他们都是不彻底的普通人,范柳原接受现代文明的影响却对传统女子情有独钟,白流苏出身于封建家庭却有着现代性的追求。白流苏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在传统文化与新文化强烈碰撞交织下的女性生存悲剧。白流苏知道“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一个男人,是一件艰难的、痛苦的、几乎是不可能的”,[2]60然而最终却还是败下阵来,为了生存同意做范柳原的情妇。柳原意在求欢,流苏欲在求生,这是一个女人最根本的悲哀。这一段倾城之恋反映出女性在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求生的艰难。在男权社会里女人们想尽全力来博取男性的欢心,因为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婚姻上。白流苏不过是这其中的一个,婚姻在她们眼中是终极的目标。旧式家庭中走出来的白流苏们不可能成为革命女性,她们所有的付出都是为了出嫁,这个卑贱却是她们全部赌注的希望,折射出的是整个女性在社会中的生存悲剧。香港的战争使得流苏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婚姻,使得社会悲剧在白流苏身上的表现增添了几分戏剧化的色彩。“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2]87这真是对白流苏身上体现出的社会悲剧的完美诠释。“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2]85在这样兵荒马乱的背景下奇迹般地出现生命和爱——究竟是对美好生命的希冀,还是对黑暗现实的讥讽?但不管如何,这最终使流苏和范柳原“走向了平实的生活” [2]85,两人的关系由谈情说爱变成了“恋爱”和“透明透亮的知遇” [2]85,可以在飘摇中“一刹那的彻底地谅解,……在一起和谐地活上十年八年。”[2]85
在散文《烬余录》中,张爱玲曾说过:“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吗?事实是如此。”[4]张爱玲说话就是这般一针见血。从解构主义的角度来分析,“这篇小说中,通过两个主人公的‘倾城之恋’,解构了爱情神话,浪漫的爱情不过是经济的依靠和生理的满足。通过白流苏同家人的矛盾,解构了亲情神话:哥哥嫂子不过算的是金钱帐,母亲无力庇护自己的儿女。同时,作品还解构了自由意志的神话,范柳原和白流苏都以为能够做得了自己的主,却发现在社会和命运两只巨手之下,个人只能沉浮于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支配之下。”[4] 作者在几分哀怨、几分落寞、几分悲戚、几分宿命中,展现了人在金钱和战争前的无奈与脆弱,对文明的命运和人性中的真与假发出了最挑衅的逼问。
张爱玲笔下典型的男女有许多,除了范柳原和白流苏之外,还有沈世钧和顾曼桢。“火车开了,轰隆隆离开了南京,那古城的灯火渐渐远了。人家说‘时代的列车’,比喻得实在有道理,火车的行驶的确像是轰轰烈烈通过一个时代。”[1]64传统的思维通过相隔遥远的时空来影响着人们的行动,微妙而又危险。火车轰隆一瞬,沈世钧和顾曼桢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半生的情深缘浅注定了这一段漫长却悲哀的不了情。这一趟“时代的列车”仿佛带我们走过了一遭《半生缘》里男男女女一幕又一幕的过去和现在,心底里透出一丝悲凉。曼桢的父亲早逝,姐姐曼璐为养家踏入红尘,放弃了恋人张豫谨,后来嫁给了投机分子祝鸿才。曼璐因不能生育企图劝曼桢当其夫的姨太太,遭曼桢拒绝,她居然协助鸿才强暴并软禁了曼桢,令曼桢和世钧从此阴差阳错、相隔天涯。这一场劫难送走的是他们的幸福生活,也送别的是曾经的自己。只好用淡然疲惫的目光,将曾经因其而沸沸扬扬,以后无他依旧沸沸扬扬的尘世关在了门外。世人再如何评论,他们也已经再不关心。这一幕幕纠缠不清的感情,独具风格地展示了一场红尘情爱。原以为因为爱而结合是完美的,但是,以爱的名义谋杀爱的事情比比皆是。“世钧,我们回不去了。”[1]288不是时光没有等待曼桢,而是世均没有把她带走。究竟是什么令这一对璧人擦肩而过?是顾曼璐的自私愚蠢?是祝鸿才的泯灭人性?是沈世钧的懦弱放弃?不!最是刺人心锥的封建社会道德伦理!小说中的曼桢她是那么的坚强,贫困的家庭,失意的爱情,姐姐的陷害,母亲的不解,姐夫的残害,命运的安排,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无情打击着她,我难以想象那么单纯柔弱的她是如何在面对,在小说的最后她应该是心凉了,为了生活她只能选择和祝鸿才这个毁了她所有幸福的恶人在一起,就是这样让人心痛的选择导致事情的结局越出了人们的可以想象的范围,而张爱玲的目的也就在于此,用最冷静的文字告诉人们,这才是现实和生活的本质。
《半生缘》里真正值得同情的不是男女主角凋谢的爱情,而是曼桢软弱无助的悲惨命运。她对爱情的执着远远比作品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坚定,在这一点上,曼桢是一个传统得入骨的女人。她听着马路上“汽车行驶的声音”[1]166,这个现代的意象似乎是这个传统的女子急于挣脱困守着她的牢笼的希望,但哪怕她再如何“侧耳听着外面汽车的声音” [1]166,都没有人救她,都无法改变她被姐姐、姐夫一手摧毁的命运。越是现代的东西,越难以摆脱传统的意味,现代女性和古代女性最内在的观念,始终如一,那就是面对情爱的归宿感。虽然物质追求、拜金主义、金钱压力令现代的爱情观扭曲不堪,但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人无限膨胀的欲望,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外在的光怪陆离改变不了的是女性对爱和安全感的渴求。
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哪一条路能走进一个人的内心?马路宽广,但心路狭窄,汽车一路向北,漂泊无依的孤独感何时能找到心灵的归宿?心灵的空虚跟随着汽车的前进而漂移,天大地大,哪里才能容得下一个小女子不堪一击的爱情?日月不掩,春秋代序,汽车仿佛载着人们走过了古今,踏遍了人生。古往今来,每天走着同样的路,却看着不同的人上演着人生的悲欢离合,张爱玲用一辆简单的汽车带着读者们一同和书中的主人公,走了一遭如浮萍般漂泊的人生,让人揪心的不仅仅是那一对对分开的璧人和一个个没有结局的爱情故事,而是人经过万分挣扎、淌尽苦泪之后回首凝望,却仍是无根、无家、天涯处处无归宿的悲凉。这才是张爱玲的真实写照,她猜中了每一个人的结局,却猜不到自己的结局,莫非,这就是上天给她的结局?
四、小结:现代性的困惑
张爱玲与现代性的重大命题进化论、民族国家似乎都不相关,即使和现代性另一重大命题人文精神的个性、人道、自由、理性等特征的联系也不太密切,在她笔下,有的是生存的平凡、生命的苍凉和“越现代就越传统”的现代性困惑(当然说前两点符合现代派的精神倒是对的)。
例如张爱玲笔下的汽车意象。汽车最初的意义只是一种穿行于城市的交通工具,一种载体。但在张爱玲的视野里,它逐渐升华为承载生命的容器。汽车作为一种现代意象频繁出现在张爱玲的作品里,无疑是因为汽车的发明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大成就,它的平民化缩小了阶层之间的差异,连接着传统的人面对新兴文化所产生的矛盾和顺应思潮。汽车这一现代意象,可谓是自由穿梭于传统思想与现代观念中的特殊枢纽,不同的人坐着不同的车,但难以摆脱的却是一样的凄怆。张爱玲营造的意象,既有不厌其烦的袭旧,又有层出不穷的创新,在新旧雅俗之间游刃有余,而且,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都是与作品“苍凉”的主调是一致的。“这大量的新旧并置的物件展示了张爱玲和现代性的一种深层暧昧关系,它亦是张爱玲小说的醒目标记。” [7]291 不管是现代性的建筑如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还有马场,还是印刷文化——“从书刊进入‘一个奇异的新世界’” [7]138 ,还有为我们带来强烈视觉冲击的电影文化,这一切逼迫站在十字路口的我们不得不思考在现代化猛烈撼动下的中国,为什么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文化在我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是心理上的失落、震撼等种种复杂的感情。浓重的色彩,繁华而无助的人生,极柔情又极冰冷,极热忱又极苍凉,直把人情冷暖层层拨开,离析了世俗生活中最残酷的真实,这就是张爱玲。
1940年代是上海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10年,太平洋战争后历经百年的上海租界宣告结束,中国抗日战争的结束意味着强大的日本势力撤出中国,而随后的国共内战,最终迫使国民党退出中国大陆,也包括上海这个主要基地。众所周知,张爱玲的文学作品都是在1940年的背景下进行的,显而易见的是,她生活在被日伪占领而远离革命尘嚣的上海,因此在她的文学创作中,并没有烽火弥漫的战争、血流成河的场面。她认为“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7]285她毕竟真实地生活在这样一个白昼如黑夜的年代,切身经历过一场深烙在她心中无法忘怀的战争,目睹香港沦为一片废墟,面对了一场场无情的生离死别,这导致她对战争时期人们心理的剖析十分深入,在字里行间弥漫着一股没有战争的硝烟味,这来自于她的乱世之感以及战争给她带来的心理刺激和精神创伤。“当香港在令人无望地全盘殖民化的同时,上海带着她所有的异域气息却依然是中国的。” [7]340在我看来,当人们的内心被现代性潮流无可救药地侵蚀时,越是现代的东西却越发难以摆脱传统的意味。张爱玲的作品完全可以用大雅大俗、传统与现代八个字来概括。在她笔下的主人公通常是生活在中国的繁华大都市里,可人物本身却是落伍的;小说的表现形式是通俗的、民族的,但所包含的思想却是现代派的;故事平庸琐屑,基调荒凉、阴沉,却把永恒的人性表露无疑……看似矛盾,但正是这多方面的有机融合,构成了张爱玲的雅俗共赏、容纳古今的传奇艺术世界,虽然她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仍然没有明确定论,但是,张爱玲是文坛的奇葩这个说法,想必是无庸置疑的。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1>长篇小说之半生缘[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2]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中短篇小说]1943年作品[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3]张爱玲.中国现当代名家精品书系——张爱玲全集[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
[4]卢长春.《倾城之恋》的反讽叙事[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7(12)
[5]许子东.《重读<日出>、<啼笑因缘>和<第一炉香>》[J].文艺理论研究,1995,(6)
[6]费勇.《张爱玲传奇》[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7]李梵欧.《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LIFE THAT CANNOT BE TAKEN AWAY BY CAR
——BRIEFLY ANALYS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AR ACCORDING TO ZhANG AI-LING’S NOVEL
Libaoying
The Depa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lass1, Grade 2008
No:200824051137
Abstract:The "CAR" image created in Zhang ai-ling's novels is both real and unreal, traditional and modern. It suggests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the characters and reflects their inner worlds. Moreover, it it a particular refraction of the vision of love between tradition and contemporary. In short, Zhang ai-ling's small car, implies the trasition of times and the change happened in people's heart from hopefully to desperately , is beautiful and miserable.
Key words: Zhang ai-ling;the “CAR”image;the view of love;traditons;modern times;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