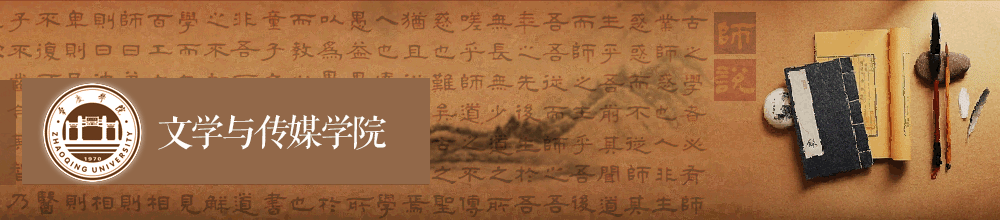余珮姗
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09级(2)班 学号200924051225
摘要:互文性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本文以《PIERROT——寄呈望舒》为核心,考察穆时英小说与戴望舒诗歌之间的互文现象,尝试探讨二者形成互文关系的原因,并从互文性角度进行对作品的解读。
关键词:互文性;穆时英小说;戴望舒诗歌
一、 互文性概念简介
互文性作为一种重要的现代文本理论,首先由法国符号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提出,她认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1]伴随着互文性概念同时出现的,是文本的新的意义,即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
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其作品《误读图示》中指出:“一切文学文本都必然是一种‘互文本’,任何文本的根据都是另一个文本。”[2]这一说法否定了文学文本自身绝对独立的观念,使文本在相互间形成了必然的联系。
耶鲁大学著名文学批评家杰弗里·哈特曼也在《作为文学的文学批评》中,推动了不确定性原则的发展,表明文学语言及文本含义之间存在互相转换、互相包容的可能。
经过文艺理论家们对互文性概念的不断阐释与发展,互文性现象日益受到重视。人们清楚意识到,互文现象存在于文本中的普遍性。每一种文本类型存在于巨大的文本世界中,都不可避免地彼此指涉、渗透、转化和扩展。[3]
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互文性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4]本文将以穆时英小说与戴望舒诗歌为例,研究不同作家不同文体作品的互文性。
二、 戴望舒诗歌与穆时英小说形成互文的可能
1905年,戴望舒出生于浙江杭州,在母亲的温柔照料下,在充满诗情画意的西湖边,他受到了古典文化的滋养与熏陶,细腻的情感在不知不觉中丰富着他的内心。上学后的戴望舒长期接受保守的传统思想教育,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春风吹来,他开始接受外来的思想文化,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在新诗发展中,诗人戴望舒以最少作品成为了现代诗派的举旗人,领袖了一个重要的艺术流派。随着代表作《雨巷》的发表,戴望舒获得了“雨巷诗人”的美誉。可以说,戴望舒诗歌中哀婉感伤的浓重气息,早已让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现代诗坛上再没有如此浓郁的愁情诗人。
然而,在诗歌中独一无二的忧郁身影,却出现在几乎同一时期的小说文坛上,那便是戴望舒当年的好友,也是戴望舒后来的小舅子——人称“鬼才”、 “新感觉派圣手”,为一时风行的海派作家穆时英。
穆时英的出身和戴望舒有着不少相同之处:出生于浙江,在温柔的母爱下,度过安逸幸福的童年,性情中带有浪漫与敏感的特质;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成长于新旧文化交替之际,积极吸收外来文化思想,从中学时期开始表现出过人文学天赋,随后考入上海的大学,融入崭新的大上海文化氛围。
戴望舒与穆时英这两位来上海求学的年轻人,在五光十色的都市大环境中,都很快地接纳了上海的都市文化,不仅对大都会的生活方式非常适应,对各种现代娱乐方式更是着迷。他们跟上了都市生活的快节奏,习惯在饭店、电影院、歌舞厅、跑狗场等消费场所寻找刺激与享受。就连戴望舒在追求初恋情人施绛年期间,也有过出入歌舞酒寮的经历,其诗中的百合子和八重子就是他在那些场合认识的日本女子,逢场作戏在二三十年代的文人中不算什么。[5]92
然而,在都市光鲜的背后,更多的是黑暗。长期生活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在发现都市之美的同时,两颗敏感的心也发现了都市之恶。故戴望舒与穆时英对现代都市文化迷恋的同时,并不能全盘地认同与接受,而是保留批判的态度,因而不愿意让自身被完全地现代化、都市化。加之二人均来自浙江城镇,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情怀根植在心中。即使已离开家乡故土,但却深知自己的根并不属于脚下华美的土地,故二人长期生活在都市,却无法真正地融入都市。尽管两位青年作家在文学才华上颇为自我欣赏,但依然无法掩饰因出身而造成的不适应感,从而陷入了都市生存的尴尬境遇。因此,二人对待都市的态度始终呈游离态。这种矛盾的情感价值反应在文学作品中,便是大量关于都市生活的幻影与感伤、迷恋与批判。
以穆时英为代表的海派作家的创作是接续着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商业性来突围,坚持走都市小说的创作道路;而戴望舒则由林译小说和鸳鸯蝴蝶派的时代开始吸收新文化,埋下日后学习西方文学的种子。可以说,这两位青年文学家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鸳鸯蝴蝶派都市文学的影响,体现明显的是创作中的幻灭情绪。对于正处于对现实不满意,对未来很迷惘,对人生很无奈,而且正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来说,这尤其容易引起心理上的强烈共鸣。[5]16而思想精神上的相互理解,正是文人交友的基础。
1933年2月穆时英出版小说集《公墓》,他在《自序》中写道:“我要把这本书献给远在海外笑嘻嘻的PIERROT,望舒。”[6]235在1934年,他又在《现代》第四卷上发表了《PIERROT——寄呈望舒》(PIERROT可译为法国童话剧中的角色,亦可译为男吟游诗人,在此取后者之意)。由此可见,戴望舒与穆时英私交很不错。
1935年,戴望舒从法国归来,取消了与施蛰存妹妹施绛年的婚约后,回到上海重会老友,借宿在刘呐鸥家中,同住的还有穆时英和杜衡等人。穆时英在1935年6月7日给叶灵凤的信中写道:“这几天,我们这里很热闹,有杜衡,有老刘……有老戴;白天可以袒裼裸裎坐在小书房里写小说,黄昏时可以到老刘花园里去捉迷藏,到江湾路上去骑脚踏车,晚上可以坐到阶前吹风、望月亮、谈上下古今。希望你也搬来。”在6月28日给施蛰存的信中,穆时英写道:“老戴这几天,天天到我们这里来,来了就到乡间去散步。我到近来才发现他在写诗以外,还有一种特长与嗜好。他打狗的本事真不错!在这一礼拜中,他至少打了十七头野狗。”[5]138文人当中能进行文学交流的文友不在少数,但能够像这样共同创作、全面了解的文友确实不多。
在戴望舒经历初恋挫败以后,穆时英主动将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戴望舒。两人相识后,很快便坠入爱河。 1936年6月,戴望舒与穆丽娟结婚,成为了穆时英的妹夫。
由于戴望舒与穆时英的关系之亲、交情之深,再加上相近的情感价值与文学趣味,使二人在无形中产生了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在现实生活中,由朋友成为了家人;在文学创作中,通过诗歌与小说两种文体相互照应、相互解释。
穆时英多次在自己的小说中,巧妙地镶嵌戴望舒的诗句,使其小说与戴望舒的诗歌形成多处互文,应用之妙,近乎神来之笔。本文将以穆时英的小说《PIERROT——寄呈望舒》为例,对穆时英小说与戴望舒诗歌进行总体基调的大致感受和互文关系的具体分析。
三、 忧郁基调互文
1927年戴望舒的《雨巷》问世,有如一幅江南水墨画,传神地描绘出一条充满潮湿气味与忧郁情绪的江南雨巷。作为戴望舒当年的好友,穆时英在小说《PIERROT——寄呈望舒》开头的第一句,就让人明显地嗅出同样潮湿的气味:
笼罩着薄雾的秋巷(《PIERROT》)
“巷”,作为全句的中心词,在“薄雾”的迷蒙与“秋”的寂寥的作用下,和戴望舒的“雨巷”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为戴望舒与穆时英的文本共同构建了幽深狭窄的空间,似乎暗喻处境的封闭与不明朗,营造出沉寂苦闷的情调。
从大致总体上品读作品,可以初步感受到与戴望舒诗歌相似的忧郁基调:
‘Traumeri’——那紫色的调子,疲倦和梦幻的调子(《PIERROT》)
“traumeri”翻译成中文为梦幻曲的意思。“紫色的”“疲倦和梦幻的”梦幻曲,直接地让人的脑海中浮起这旋律:
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她飘过,像梦一般地,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雨巷》)
所谓的梦幻曲,似乎指的正是望舒的《雨巷》——一首艺术美的结晶。穆时英运用通感的手法,将视觉、听觉等感官直觉相结合,将《雨巷》中紫丁香的色香、惆怅的情感、飘渺的虚幻感以及那萦绕不断的忧郁情怀糅合在一起,以缓慢慵懒的姿态铺展开来,奏出低沉而优美的调子,一方面,以细腻的笔触通向他的现代主义风格,另一方面,不断地吸收戴望舒诗歌的忧郁气质。如:
在那路灯的,潮润的,朦胧的光幕底下,迈着午夜那么沉静的步趾,悄悄地来了潘鹤龄先生,戴着深灰色的毡帽(《PIERROT》)
这处文段,是对戴望舒《夜行者》的拟仿:
你看他走在黑夜里:戴着黑色的毡帽,迈着夜一样静的步子(《夜行者》)
穆时英让戴望舒诗歌中的夜行者走进了自己的小说,依然是黑暗的形象、沉默的姿态,行走于黑暗环境,成为黑暗里的一部分,与黑夜融为一体。
又如:
不知哪一间屋子里的钢琴上在流转着Minuet in G;这中古味的舞曲的寂寥地掉到了水面上去的落花似的旋律弥漫着这凄清的小巷。凄清的季节!凄清的,凄清的小巷啊!(《PIERROT》)
这一文段映射出了两首诗歌的影子:
从水上飘起的,春夜的mandoline,你咽怨的亡魂,孤冷又缠绵……你依依地又来到我耳边低泣;啼着那颓唐哀怨之音;然后,懒懒地,到梦水间消歇(《Mandoline》)
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地,默默彳亍着,冷漠,凄清,又惆怅(《雨巷》)
穆时英将曼陀铃的中古味旋律与雨巷的凄清意境巧妙结合,让听觉神经与视觉画面交错相织,在大脑记忆中似萦绕不断,又淡远消散。
再如:
和寂寥的琴声一同地,他的心房的瓣一片片的掉下来,掉到地上,轻灵地。他觉得有一些寒冷,是的,一些寒冷和一些忧郁,牧歌那么冲淡的忧郁 (《PIERROT》)
穆时英笔下的这些“寒冷”和这些“忧郁”,正与戴望舒笔下的那些“寒冷”和那些“忧郁”相互对应:
迢遥的牧女的羊铃/摇落了轻的树叶……唔,现在,我是有一些寒冷,一些寒冷,和一些忧郁(《秋天的梦》)
迢遥的羊铃与寂寥的琴声相对应,轻的树叶与心房的瓣相对应,有形的轻与无形的重相对应。尽管穆时英变换了文本语言,却不改变所指。轻灵的飘落,依旧负载着心头的沉重。
穆时英小说与戴望舒诗歌这种相似的忧郁基调,不仅由于修辞上或语言上的互文,也包括穆时英对戴望舒诗歌的直接引用:
——插曲——:明天会有太淡的烟和太淡的酒,和磨不损的坚固的时间,而现在,她知道应该有怎样的忍耐,托密已经醉了,而且疲倦得可怜——插曲——(《前夜》)
《前夜》通过来日漫长无味的岁月,表达今夜欢愉的短暂。因为短暂,所以难忘。穆时英借南方少年与托密的离别,跟小说主人公潘鹤龄与琉璃子的离别形成互文,表现潘鹤龄与琉璃子内心的难离难舍,赋予了《前夜》全新的完整的故事背景。
文本之间欲营造相似的基调,既需要内在元素,也需要外在框架:
她的眼珠子里边有一些寒冷,是的,一些寒冷和一些忧郁,牧歌那么冲淡的忧郁……他太息了一下,在自己脚下捡起了掉到地上的心房的瓣,把中古味的舞曲,Minuet in G,仍在后面,往前面走去,悄悄地。就和她来的时候一样悄悄地,隐没到笼罩着薄雾的秋巷的那边(《PIERROT》)
一切仿佛呈现海潮回流的现象、播放机倒带的状态,终点处又回归到起始处,巧妙的回环体形式与戴望舒的《烦忧》形成结构上的互文,使字里行间富有诗意和诗韵:
说是寂寞的秋的悒郁,说是辽远的海的怀念。假如有人问我烦忧的原故,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假如有人问我烦忧的原故:说是辽远的海的怀念,说是寂寞的秋的悒郁(《烦忧》)
乐音缭绕、回环往复,内心的真实情感欲扬欲抑、欲言又止,使忧郁的思绪萦绕不断。诗歌并没有足够的空间让诗人细诉他心底烦忧的缘由,我们所感受到的忧郁基调,是诗人通过诗歌表达的心绪起伏,是一种“隐藏的表现”。然而,小说的三要素却正好弥补了诗歌缺失的表达空间,向读者展现故事完整的人物、情节、环境。
四、 场景隐与显的互文
大上海的霓虹幻影映照了青年作家的脸,被反射到作家们的笔下,描绘出了现代都市的纷繁与忧伤。诗人戴望舒通过古典意象以抒发都市情感,含蓄委婉;而小说家穆时英则用犀利大胆的笔锋勾画现代文明的真实写照:
街有着无数都市的疯魔的眼:舞场的色情的眼,百货公司的饕餮的蝇眼,‘啤酒园’的乐天醉眼,美容室的欺诈的俗眼,旅邸的亲昵的荡眼,教堂的伪善的法眼,电影院的奸猾的三角眼,饭店的朦胧的睡眼……桃色的眼,湖色的眼,青色的眼,眼的光轮里边展开了都市的风土画(《PIERROT》)
此段关于都市生活情景的象征性写法,与戴望舒的《灯》极为相似:
作憧憬之雾的/青色的灯,作色情之屏的/桃色的灯。因为我们知道爱灯,如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为供它的法眼鉴赏/我们展开秘藏的风俗画:灯却不笑人的风魔。在灯的友爱的光里,人走进了美容院;千手千眼的技师,替人匀着最宜雅的脂粉,于是我们便目不暇给(《灯》)
戴望舒借助灯的光芒,照亮现代文明与都市人生活的密切关系,表现都市人对美与享受的追求,以及男欢女爱、活色生香的夜生活。诗人通过灯之意象,探索都市在白天里隐藏的每一面,不仅挖掘出现代人对都市的迷恋,还反映了物质文明、商业文明对现代人生活方式及思想精神的巨大影响。
而穆时英则在戴望舒的描绘基础之上,将“灯”化作“都市风魔的眼”,安排更具体的现代都市场所,使都市人形形色色的内在欲求展露无遗,并在“灯的友爱的光里”进行着、释放着,构成一幅原汁原味的“都市风土画”。
作为一位新式洋场小说家,穆时英把新感觉的文体,发挥得淋漓尽致。是他创造了心理型的小说流行用语和特殊的修辞,用有色彩的象征、动态的结构、时空的交错以及充满速率和曲折度的表达式,来表现上海的繁华,表现上海由金钱、性所构成的众声喧哗。其新感觉派小说,在现代文学式上第一次使得都市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可供品赏,同时进行一定的文化思索。[7]252如《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等作品,以其丰富精彩的都市描写,赐予读者感官细胞的舒张膨胀,打造身临其境的逼真感。
然而,穆时英的城市意味是复杂的。在戴望舒的诗歌中,他找到了共鸣,并完整地表现出这种对上海既迷恋又批判的双重态度[7]252:
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调化妆着的都市啊!(《夜总会里的五个人》)
木叶的红色,木叶的黄色,木叶的土灰色……红色,黄色,土灰色,昏眩的万花筒的图案啊!(《秋蝇》)
穆时英吸收了戴望舒《秋蝇》中象征与夸张的表现手法,以五彩变幻的色彩光潮刺激读者的视觉感官,叙写现代都市纷繁杂乱的万花筒世界。其极富张力的表述,将秋蝇的神经衰弱的敏锐感觉和独特的个体生命体验,带入真实的生活境遇,在迷恋都市的同时,批判现代人浮躁的、失衡的都市生活模式,暴露人们在神经上及精神上的强烈压迫感与疲倦感,真实地还原了戴望舒在《秋蝇》中所隐藏的都市感受。
又如:
华东饭店里——
二楼:白漆房间,古铜色的雅片香味,麻雀牌,《四郎探母》,《长三骂淌白小娼妇》,古龙香水和淫欲味,白衣侍者,娼妓掮客,绑票匪,阴谋和诡计,白俄浪人……
三楼:白漆房间,古铜色的雅片香味,麻雀牌,《四郎探母》,《长三骂淌白小娼妇》,古龙香水和淫欲味,白衣侍者,娼妓掮客,绑票匪,阴谋和诡计,白俄浪人……
四楼:白漆房间,古铜色的雅片香味,麻雀牌,《四郎探母》,《长三骂淌白小娼妇》,古龙香水和淫欲味,白衣侍者,娼妓掮客,绑票匪,阴谋和诡计,白俄浪人……(《上海的狐步舞》)
木叶,木叶,木叶,无边木叶萧萧下(《秋蝇》)
穆时英与戴望舒均习惯使用单调的重复修辞手法。在这组互文中,二人分别描写了都市人与秋蝇的个体视野,却表现了极为相似的生存困境。在《秋蝇》中,戴望舒以“木叶”取代“无边落木萧萧下”中的“落木”,成为失意悲伤之寄托物。而漫天飞舞的,除了木叶,还是木叶,彻彻底底地表现生命的卑微渺小与生存之苦。同样的单调的重复被穆时英采用于《上海的狐步舞》中,叙写出了都市人单调机械的都市生活、单调乏味的精神世界、无营养无价值的存在模式以及无休止的欲望与罪恶,彻彻底底地表现出都市人的无聊空虚的苦闷生活。
由此可见一个微妙的现象:戴望舒诗歌与穆时英小说中所抒发的都市情绪,默契地达成了高度一致;而戴望舒诗歌中所隐去的场景,却在穆时英小说的都市环境描写中得以找到。
五、 情绪藏与露的互文
实际上,除了批判——迷恋,穆时英的现代派十足的作品内面,始终还有第三重的审美意味,就是潜在的哀婉抒情气息。这是他作为中国文化传接者无法摆脱的。[7]252以哀婉抒情气质而闻名的“雨巷诗人”戴望舒,早已让人们认识了《雨巷》中哀婉忧愁的丁香姑娘。而在《PIERROT——寄呈望舒》中,穆时英也叙写了一位同样哀婉忧愁的琉璃子:
潘鹤龄先生站住了,望着巷尾一百二十号二楼的窗,在那里有他的琉璃子,发香里簪着辽远的愁思和辽远的恋情的琉璃子
她的眼是永远茫然地望着远方的,那有朴素的木屋,灿烂的樱花和温煦的阳光的远方的,那么朦胧地,朦胧到叫人流泪地(《PIERROT》)
穆时英对日本女子琉璃子的描写,与戴望舒的《八重子》《百合子》有着明显的相似性:
发的香味是簪着辽远的恋情,辽远到要使人流泪……忘记萦系着她的渺茫的乡思 (《八重子》)
百合子是怀乡病的可怜的患者,因为她的家是在灿烂的樱花丛里的……但温煦的阳光和朴素的木屋总常在她的缅想中……她盈盈的眼睛茫然地望着远处(《百合子》)
琉璃子与八重子、百合子同为温柔的日本女性,不仅具有典型东方女性的婉约气质,还富有辽远的乡思与恋情,这也是怀乡病者普遍的忧郁根源。
博尔赫斯说,作家以为自己在谈论很多事情,但他留下的东西,假如他运气的话,是一幅他自己的形象。戴望舒“自己的形象”就是那个忧郁的徘徊在雨巷中的诗人。[5]90正因为戴望舒是一个忧郁的主体,他的创作作品及对象必定带有这种忧郁的主体情绪,这是一种同化的过程。诗人习惯性地以自身气质同化了八重子与百合子,使她们成为诗人自身的影子。故可得知,诗人在创作中偏爱的女性形象,无疑是丁香姑娘般忧郁的女子。
穆时英在接受戴望舒影响的同时,对这种忧郁气质极为敏感与关注,并塑造了走同样忧郁路线的琉璃子。但是,八重子与百合子毕竟是戴望舒在歌舞酒厅中认识的日本女子,单纯的忧郁气质恐怕只能让诗人产生短暂的好感,未能借此表达潘鹤龄对琉璃子的深爱。于是,便有了以下几处对《我的恋人》的拟仿:
琉璃子有玄色的大眼珠子,林檎色的脸,林檎色的嘴唇,和蔚蓝的心脏
可是当她倚在他肩头的时候,便有了蔚蓝的,温存的眼珠子……(……温存的,蔚蓝的眼珠子,她的心脏的颜色的眼珠子)
“很早就等着了吗?”温柔到消融我的心的声音(《PIERROT》)
这些对琉璃子的描写,都与戴望舒对恋人的描写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我将对你说我的恋人,我的恋人是一个羞涩的人,她是羞涩的,有着桃色的脸,桃色的嘴唇,和一颗天青色的心。她有黑色的大眼睛……而当我依在她胸头的时候,你可以说她的眼睛是变换了颜色,天青的颜色,她的心的颜色……她有清朗而爱娇的声音,那是只向我说着温柔的,温柔到消融了我的心的心的话的(《我的恋人》)
如此相似的纯净可爱的恋人形象,同时住在了戴望舒与潘鹤龄的心里,毫无保留地展现了潘鹤龄内心与戴望舒高度一致的恋爱心理。
值得玩味的是,在女性身上,这份纯净可人与上述的忧郁婉约相结合,便是诗人戴望舒与小说人物潘鹤龄共同的挚爱。当然,戴望舒从没有明确表示,只是通过诗歌中的只言片语欲言又止。而穆时英却借潘鹤龄之口,在餐桌上替戴望舒说出了诗歌中隐藏的话语:“牛排!除了性感,她们的爱娇便等于零;西洋人真是牛排!只有东方人是灵感的;琉璃子的婉约味在她身上一点影子也不会有的。”(《PIERROT》)这种灵感的婉约味,超越了对女性肤浅的外貌审美标准,不仅是潘鹤龄的精神依恋,也是戴望舒的理想女性形象,更是他对灵魂美的追求。
在穆时英的不少小说作品中,也出现了相似的女性形象,比如《公墓》的女主人公欧阳玲。她是“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有着“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纯洁可爱的外表下,散发着忧伤与古典的气息,叫人心里既怜悯又爱慕。
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戴望舒与穆时英这种对女性内蕴的追求的一致性,形成了他们共同的哀婉抒情的审美意味,这使两位作家的作品在有意与无意间构成了同义互文:
“看我的眼吧,它们会告诉你什么是热情,什么是思恋,什么是我的秘密,什么是我的嘴不敢说的话,什么是我每晚上的祷辞。”
羞涩的夜合花似的,琉璃子低下了脑袋,在嘴边藏着微笑(《PIERROT》)
作为我们心灵之窗,眼睛,在文学创作当中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戴望舒诗歌中的主人公便是常常这样,通过眼睛作最深入的灵魂对话,营造出一个精神层面的、形而上的、理想的二人世界,让尘世间的男女之情脱掉俗味,使情感交流获得极致的升华:
因为我们的眼睛是秘密地交谈着;而她是醉一样地合上了她的眼睛的,如果我轻轻地吻着她花一样的嘴唇(《百合子》)
不要怕我发着异样的光的眼睛,向我来:你将在我的臂间找到舒适的卧榻(《到我这里来》)
我的小恋人,今天我不对你说草木的恋爱,却让我们的眼睛静静地说我们自己底(《款步一》)
穆时英向戴望舒借来了诗人的眼睛,让潘鹤龄在幻想中,通过眼睛这一心灵窗口,尽情地把自己的内心作无声表达,期盼换来诗歌中娇羞恋人的动人表现:
恋之色的夜合花,佻达的夜合花,我的恋人的眼,受我沉醉的顶礼(《三顶礼》)
而当她想到在泉边吻她的少年,她会微笑着,抿起了她的嘴唇……他或许会说到她的女儿的婚嫁,而她便将羞怯地低下头去(《村姑》)
愿望总是美好的,而现实却未必都能如愿。就像作家通过作品表达自己的内心,却不一定能得到正确的解读:
他们从他的作品里发掘了跟他所表现的主题完全不同的主题来。譬如说,在他写的时候只抱着一种抒写初恋的蜜味的短篇《园》里边,荣哲人先生说他是在写一个十八岁的处女的感情,高令德先生以为是写有闲阶级的恋爱游戏,包咨先生赞叹着他的句法,黎尊先生说他只是写苍蝇与初恋的关系,金仲年先生改正了荣哲人先生的意见(《PIERROT》)
故事中潘鹤林所写的这篇倍受分歧的作品《园》,似乎在暗指戴望舒的一首短诗《深闭的园子》:
五月的园子/已花繁叶茂了,浓荫里却静无鸟喧。小径已铺满苔藓,而篱门的锁也锈了——主人却在迢遥的太阳下。在迢遥的太阳下,也有璀璨的园林吗?陌生人在篱边探首,空想着天外的主人(《深闭的园子》)
诗歌到底在写无人问津的寂寞园子,不甘寂寞的园子主人,还是思恋少年的花季少女,众说纷纭。读者从不同视角出发,对总分意象的各种理解,都能创造出不一样的解读,而往往大多数的版本并非作者的原意。
穆时英早期发表的作品,在文坛上的确曾经引起颇大的分歧,有人赞赏,也有人批评,甚至许多评论家的理解与他想表达的意义存在较大的出入。穆时英觉得“世界上顶稀奇的事是有人会把你的小说解释得和自己的意思完全不同,而我就是常碰到那种奇迹的人”。[6]233或许因此,他参照戴望舒一首同样被多重理解的《深闭的园子》,在《PIERROT》中赐予潘鹤龄同样的作家生活体验。因为缺乏理解,或害怕被看穿,潘鹤龄始终需要被理解与支持,他渴望一个忠实于他的灵魂的身影,替他驱赶精神上的孤单:
她是我的影子,她是我的妹子,她是忠实于我的!琉璃子啊!琉璃子啊!
“琉璃子,你是忠实于我的吧?”
“象你的影子一样忠实于你的” (《PIERROT》)
潘鹤龄对“忠实的”琉璃子万分珍爱,就像诗人戴望舒珍爱自己的记忆一样:
我底记忆是忠实于我的,忠实得甚于我最好的友人……在一切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东西上,它在到处生长着,像我在这世界一样(《我底记忆》)
正如诗歌所描绘的,戴望舒的记忆无论是真实的心理记录,或是微妙的内心情愫,都是永远忠实于他的。一切游离于虚实苦乐间的记忆都源于生活中最敏感、最自然之处,与诗人的思绪保持一致,伴随诗人生命的始终,如影随行。
如上所述,穆时英也曾陷入不被理解的困境,他所作出的反应是“说我什么都可以,至少我可以站在世界的顶上,大声地喊:‘我是忠实于自己,也忠实于人家的人!’”[6]233穆时英在戴望舒的诗歌中找到共鸣,并对小说中的潘鹤龄安排同样的困境,使他在精神上渴望被正确解读,却在精神上被陌生化、边缘化。
这正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沟通屏障与精神隔膜,对周边的人事物看不清、摸不透,亦是现代人寂寞空虚的苦闷情绪的一大来源。尤其是当一个渴望忠诚的人,遇上一个不安定的灵魂:
偎在我胸前的琉璃子也一样偎在别人的胸前;她对我说:‘象你的影子一样忠实于你的。’也对别人说:‘象你的影子一样忠实于你的。’她在我的肢体的压力下,也呈着柔弱的花朵的姿态,在别人的肢体的压力下也呈着柔弱的花朵的姿态;她在我的肩头,有着温存的,蔚蓝的眼珠子,她的心脏的颜色的眼珠子,在别人的肩头,也有着温存的,蔚蓝的眼珠子,她的心脏的颜色的眼珠子;她的辽远的恋情和辽远的愁思是属于我的,可是也属于别人,属于二个人,三个人,几十个,几百个,几千几万个人,不,是属于每一个生存着的人的,琉璃子,我的憧憬,我的希望,我的活力的琉璃子,不是我的,而是每一个生存着的人的(《PIERROT》)
此段为对潘鹤龄内心思绪的描写,恰与戴望舒的《路上的小语》构成一组反义互文:
——给我吧,姑娘,那在你衫子下的/你的火一样的,十八岁的心,那里是盛着天青色的爱情的。——它是我的,是不给任何人的,除非别人愿意把他自己底真诚的/来作一个交换,永恒地(《路上的小语》)
戴望舒也渴望着一个完整的、忠实的伴侣。出于爱情的自私性和男性的占有欲,诗人以恳求的口吻,希望用自己的爱情,去交换少女的真心。
与望舒的“不给任何人的”爱情愿望相比,小说中潘鹤龄的爱情则显得可悲得多。在琉璃子身上柔美的一切,不止属于潘鹤龄一人,也属于每一个生存着的人;不是只给潘鹤龄的,而是可以给任何人的。但也不排除,这可能是穆时英在隐晦地披露戴望舒的苦恋,即与诗人美好愿望相反的真实境况。
戴望舒与穆时英不约而同地在创作中表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反映出都市人的在受挫后对理想的失望。哪怕是一句无心的话语,也可能引发心中的怒火:
和我一同地睡在这张床上,说着要消融我的心的,温柔的话,就在这张床上,你又在别人的耳朵旁边说着‘拥抱我吧’的话!畜生!淫贱的畜生!(《PIERROT》)
“追随我到世界的尽头,”你固执地这样说着吗?你说得多傻!你去追随天风吧!我呢,我是比天风更轻,更轻,是你永远追随不到的(《林下的小语》)
在恋爱过程中,敏感多虑的诗人,时常小心翼翼地在自恋与自卑中徘徊。当调皮的恋人表现出浮云般飘忽不定时,诗人便感到爱情的若即若离、捉摸不透,并开始厌倦这种无休止的追逐游戏。或者说是,因无法得到,而自我抽离。
小说里,穆时英在全新的人物故事语境下演绎了戴望舒诗歌中传统的爱情危机。表现了都市人在寻梦过程中,一次次的迷失自我与一次次的重拾自我,对理想与爱情不断产生新的认识与定位。由此,穆时英将戴望舒诗歌深处含糊的都市情绪具象化,凭借小说的文体优势,替戴望舒的创作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如文章开头所阐述,戴望舒与穆时英对于都市的情感态度始终呈游离态,自然之子面对都市生活的重压,内心始终渴望温暖的家园:
生理的失节,给我的不过是浅薄的妒忌,可是灵魂的失节,琉璃子啊,是会使我变成幽魂的(《PIERROT》)
我呢,我渴望着回返/到那个天,到那个如此青的天,在那里我可以生活又死灭……这心,它,已不是属于我的,而有人已把它抛弃了/像人们抛弃了敝舄一样(《对于天的怀乡病》)
天,是中华文化信仰体系的一个核心。对于戴望舒而言,天可能象征着温暖的故乡、慈爱的母亲、可爱的恋人,也可能是这些美好对象的抽象综合体,共同构成诗人的灵魂寄托、生命之根。一旦失去,便被掏空,只剩下一副无心的躯壳。
在穆时英的《PIERROT》中,琉璃子对潘鹤龄肉体与精神上的背叛,使依赖女性的男子失去精神归宿,成为戴望舒诗歌中的怀乡病患者:
他轻轻地抽出了自己的胳膊,走下床来,抚着发热的脑门,一个病了的老人似地(《PIERROT》)
在读者看来,这位“病了的老人”似曾相识:
我是青春和衰老的集合体,我有健康的身体和病的心(《我的素描》)
戴望舒以诗歌形式为自己构作了一幅“静物写生”式的素描,用简单文字描绘真实的精神画像。其勾画不重在体型外貌,而重在心境和情绪,以忧郁形式,向读者坦白自身二元对立的矛盾体本质。
穆时英效仿这种素描手法,以主体的观察视角,将潘鹤龄这一客体作出直观的单色绘画。妙的是,借助戴望舒诗歌的影子,穆时英只需进行言简意赅的表象描述,即可刻画出人物内在的病态。
在穆时英的小说中,拥有与潘鹤龄同样悲哀的爱情故事的男主角不在少数。例如穆时英的另一代表作《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中的男主人公,爱上同样不忠实的蓉子,同样徘徊于自恋与自卑之间,从渐渐交付自己,到完全失去自我,结局也与戴望舒的《我的素描》形成互文,作为青年男子最后的自白:
用我二十岁的年轻的整个的心悲哀着(《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
悒郁着,用我二十四岁的整个的心(《我的素描》)
都市中,随处可见的伤人于无形的爱情快餐,正是商品社会和快节奏时代的产物,用它们锋利的刀叉,使一个个年轻的寻梦者的美好憧憬被无情地肢解,精神苦旅的最终只换来一颗空洞的心。然而,对于现实人生,没有人能抹杀,生活仍在继续,诗人只能往返于现实与梦想之间,作永恒的游云,在叹惋中忧郁。
穆时英在自己的小说中,用其独特创新的笔调,塑造典型的都市人物形象,演绎一幕幕现代情感故事,借助戴望舒的诗歌,大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内涵。而在小说中,人物的内心思绪的表现受到故事情节的限制,个体的情绪感受无法进行细致的、肆意的表达。穆时英通过对戴望舒诗歌的语言、意象等诗歌元素的吸收、转化,不仅使小说达到诗化的效果,还将作品中的复杂矛盾的现代情绪,藏在戴望舒的诗歌中,用隐晦的方式,使主观情绪实现彻底的释放和感性的流露。
六、 戴望舒诗歌与穆时英小说相互阐释
关于戴望舒创作的现代诗歌,施蛰存阐释为“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诗形”。[7]279其主要特征是承接早期象征诗派的传统,以及描写“现代”。与传统格律诗的最大区别,就是认为诗情胜过音律。戴望舒提出:“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8]因此现代诗歌更重视诗人情绪的抒发与思想的表达,一切创作以感觉为主,而忽略客观具象的表述。这一过程,现代诗人选择运用含蓄的意象来实现,追求诗歌意境情感的朦胧美的效果。
根据戴望舒现代诗歌的主要创作方式,可大致推断出其诗歌与穆时英小说形成互文的重要原因:
首先,正是现代派对朦胧美的追求,使现代诗歌意象含混、情绪朦胧,为穆时英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更多解释的可能。再者,穆时英小说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以感觉、节奏为先导,情节为次。这是其新感觉派小说区别于一般都市小说的明显特征,也是与现代派诗歌创作相同的主要特征。在穆时英充满小资趣味的散漫情调与刺激快感的两极笔锋之下,暗藏着一种与社会环境格格不入的挣扎,一种对生的压抑的呐喊,也是一种对美好憧憬的呼唤。或许,这完全可以作为对戴望舒现代诗歌的更深层的解读。
一方面,戴望舒的现代诗歌中表达了穆时英都市小说的都市感受与情绪,另一方面,都市小说又给现代诗歌中的都市情感提供了完整的故事背景。可以说,二者通过互文的形式,达到互补的结果。这种跨文体的互文性,打开了诗歌与小说两种文体各自封闭的文本空间,使不同文体的文本之间产生紧密的联系,形成内在的渗透,实现互融、互通的可能。由此,读者对文本作品的理解范畴亦得以大大地拓宽。
其实,这一文学现象在我国的文学作品中早已有之。例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与元代杂居作家白朴的代表作《梧桐雨》,均取材自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的历史故事,创作出广为传颂的爱情悲剧。可见,作品内在的一致性,是不同文体文本相互照应的基础。
一定的文化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现实存在的反映。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伴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进步,都市人在物质生活上走向富足的同时,却在精神生活上走向空虚。作为同样生存于都市与乡土、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边缘人,穆时英与戴望舒共同感受着古老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期的历史阵痛,又体验着波德莱尔笔下的都市文明的沉沦与绝望,以及魏尔伦诗行中的颓废的世纪末情绪。[7]280在快速的都市生活中,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给他们带来的,更多的是忧郁与感伤的“都市怀乡病”。
穆时英的新感觉派小说与戴望舒的大多数现代诗歌,共同刊登在《现代》杂志上,成为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道“现代都市风景线”,既是现代的象征,亦是都市的象征。二者怀着同样的情绪共鸣,相互包容,互相补充,相互阐释,在现当代文学领域中,形成了跨文本的互文的代表范例。
参考文献:
[1][法]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M]//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947.
[2] 哈罗德·布鲁姆.误读图示[M]//王一川.西方文论史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90.
[3]黄婉冬.从整合概念角度看诗歌的互文性[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 (1):62.
[4]陈永国.互文性[J].外国文学,2003(1):75.
[5]刘保昌.戴望舒传[M].武汉:崇文书局,2007.
[6]严家炎,李今.穆时英全集(第一卷)[G].//穆时英.公墓(自序).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
[7]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8]梁仁.戴望舒诗全编[M].//戴望舒.诗论零杂.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691.
THE INTERTEXTUALITY COMPARISON OF DAI WANGSHU’S POETRY AND MU SHIYING’S FICTION
——An investigate which focus on Pierrot——sent to Wangshu
Yu Peishan
The Depa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lass2, Grade 2009 NO.200924051225
Abstract:the phenomenon of intertextuality is common in the literature text. Different kinds of text can occur some interplay such as reference, permeate, transformation or extending. This thesis will focus on Pierrot——sent to Wangshu to discuss the intertextuality phenomenon of Dai Wangshu’s poetry and Mu Shiying’s fiction, as well as try to comprehend the modern Chinese poetry by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textuality.
Key words:Dai Wangshu’s poetry; Mu Shiying’s fiction; intertextuality